多少次,当我们的作家面对眼前瞬息万变的现实,当他们与那些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面对面对决的时候,一个恰当而不失艺术性的表达成了他们最大的难题。从浮皮潦草的现实进入到宽广、驳杂、深邃的人心,这样的写作让人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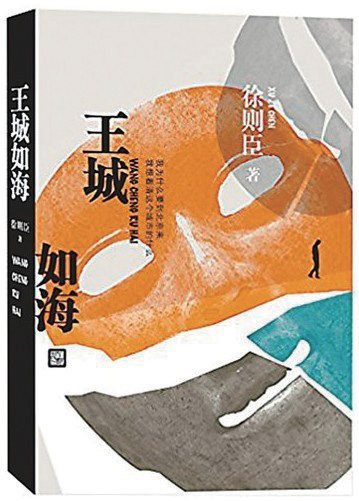
徐则臣曾经写过无数北京人,从《啊,北京》开始,《我们在北京相遇》《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等等,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卖假证的、卖碟的等城市的“漂泊者”。而在新作《王城如海》中,徐则臣将笔触对准了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成功者”:海归知识分子、知名戏剧导演,有市场号召力也有独立的艺术追求,生活中有相爱的妻子、可爱的儿子,几乎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标准的“人生赢家”。由他的故事开始,牵扯出的是生活在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中各个阶层的人们:成功者余松坡夫妇,保姆罗冬雨和她的快递员男友韩山,对未来充满憧憬和野心的大学生罗龙河、鹿茜。在他们各自的故事中,在他们彼此的相遇以及纠葛中,这个复杂而深邃的北京,它那被遮蔽的肌理被一点点扯开,那些隐藏在褶皱与缝隙中的秘密也逐渐显露了出来。
主人公余松坡的戏剧作品《城市启示录》被作者内嵌在小说之中,通过这种方式,徐则臣站在了小说主体故事的外面和前面,他更近距离地面对读者,也更直接地诉说着自己关于城市化等问题的想法。就像《城市启示录》中教授太太说的:“哦,亲爱的,怎么说呢,我看见了两个北京。一个藏在另一个里面。一个崭新的、现代的超级大都市包裹着一个古老的帝都。”小说《王城如海》中同样包藏着两个秘密:一是关于罗冬雨、韩山等所谓“小人物”的,他们的秘密属于那个“古老的帝都”,那个“既藏污纳垢,又吐故纳新,坚韧蓬勃,生生不息”的北京。这些数量庞大的“漂泊者”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他们从更广阔的农村中来,用自己几乎是属于农业文明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与北京、与现代文明硬生生地碰撞着。他们就生活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快递员、小保姆、蔬果贩……这些所谓的外来者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却是城市得以运行的巨大动力。他们白天四散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夜幕降临时回到《城市启示录》所聚焦的合租房里——那是他们的秘密集散地,也是北京这个看似光鲜的国际化大都市最隐秘的黑洞。
二是关于成功者余松坡们的秘密。罗冬雨、韩山们的困境显而易见,那是关于生存和最基本的尊严的挣扎,甚至鹿茜们的困境也不难理解,不过是想要成功的不择手段。那么余松坡和他的妻子祁好呢?他们所代表的是那个“开阔,敞亮”的北京,“那巨大的、速成的奢华假象,充满了人类意志的自豪感”。如果不是余佳山的突然出现,余松坡无疑是那种让人艳羡、钦佩并且尊重的成功者,他那些深藏在夜晚和内心深处的秘密将永远不为人知。然而余佳山的出现就像一枚深海炸弹,轰的一声,将余松坡看似美满的人生击得粉碎。他一下子成了比韩山、罗冬雨更痛苦的人,这痛苦不是生活层面的,更不是生存层面的,而是内心的、灵魂深处的。余佳山的出现让余松坡的成功瞬间失去了合法性,那外人眼里的优雅的、知识的胜利变成了一种猥琐的、钻营的胜利。这构成了余松坡人生最大的难题:一面是继续埋藏这个秘密,以保护自己已有的成功,但内心将持续被愧疚和自责所折磨;另一面是揭开这个秘密,结果很可能是丧失现有的成就和生活,但同时获得的却是内心的救赎。
在这样的困境面前,余松坡难以选择,于是他纠结、挣扎,这种内心的折磨是余松坡成功的代价,而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大都市的发展就建立在无数个余松坡走向成功的道路之上。因此,这样的代价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中国城市化的一种隐喻。“你无法把北京从一个乡土中国的版图中抠出来独立思考,北京是个被更广大的乡村和野地包围着的北京,尽管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像打了鸡血一路狂奔。城市化远未完成,中国距离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也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一个真实的北京,不管它如何繁华富丽,路有多宽,楼有多高,地铁有多快,交通有多堵,奢侈品名牌店有多密集,有钱人生活有多风光,这些都只是浮华的那一部分,还有一个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的确,余松坡,以及千千万万我们身边的所谓成功者们,其成长环境都是中国广大农村,他们走出乡土、走向城市不过是短短的十几年、二十几年,却成了所谓都市的中坚力量。他们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但却无法抹去深藏在这起点背后的价值取向、伦理观念或审美趣味。从这个层面来看,中国现代都市是可疑的,它依附于更庞大的乡土之上,这种依附不仅是地理上、空间上的,更是属于人的内心的。
罗冬雨的弟弟、在校大学生罗龙河,他几乎就是余松坡的前世,或者说,他可能就是下一个余松坡。这个余松坡忠实的崇拜者与他的偶像一样来自农村,一样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来到城市。余松坡的成功是以揭发余佳山开始的,而罗龙河也几乎如出一辙地,希望通过揭发余松坡的秘密达到报复的目的——当然,在内心深处,罗龙河渴望的绝不只是报复,更是僭越和替代。假如有朝一日罗龙河真的如愿以偿,变成了余松坡一样的成功人士,那么在他的成功道路上跟曾经的余松坡一样,也暗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一颗不知何时就会爆炸的定时炸弹。
于是,罗冬雨、韩山的困境,变成了千千万万北漂、蚁族的困境;余松坡的困境变成了罗龙河、鹿茜的困境,变成了无数走出乡村、走向城市,并一步步向着所谓“成功”进发的人们的共同困境。城市深层的分裂和对立也在这种对峙中撕裂开来:“底层”的困境和“上层”的困境是那么不同,前者是身体的、物质的,后者则是精神的、灵魂深处的;然而细细想来,似乎又没有什么区别,在它面前,没有小人物与成功人士,更没有强者与弱者。余松坡与罗冬雨、韩山一样,不过是深陷于困境中难以抽身的普通人,在那些无助的深夜,他只有在《二泉映月》的曲调中寻得片刻宁静,而这,也成了妻子祁好内心的隐痛,成了这个看似美满家庭难以启齿的暗疾。在这样的叙述中,作家将自己对于人之困境的观察和思索呈现了出来,这困境不独属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与所有人相关,因而更加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徐则臣是一个勤于并且善于在小说形式上下功夫的作家,《王城如海》中,他将余松坡的戏剧剧本与小说主体情节嵌套在一起,这样的形式在徐则臣那儿并不是第一次尝试。《耶路撒冷》中,他就曾通过“专栏”的方式,将人物内心的隐秘和思想呈现出来。这种形式让小说内部构成了对话和互文,扩张了文本的多元性和张力,更重要的是,它最大限度地容纳并且传递了作者的思想。然而,这样的形式其实很容易导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小说的主体故事情节作为一种“莎士比亚化”的艺术呈现,而剧本或专栏的部分则沦为了“席勒化”的传声筒。如此,这两个部分就成了可以割裂的两层纸、两张皮,“传声筒”变成了阻滞情节发展的累赘,仅仅满足了作者表达的欲望,对读者则失去了意义。徐则臣似乎对这个问题怀有警惕,他让这两个部分的内容通过“合租房”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看似聪明的结构背后的危险。
在涉及雾霾、快递、合租房等社会热点问题时,徐则臣与书中的余松坡一样,同样面临着表达方式的重要问题。多少次,当我们的作家面对眼前瞬息万变的现实,当他们与那些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面对面对决的时候,一个恰当而不失艺术性的表达成了他们最大的难题。《王城如海》中,徐则臣提供了一种属于他的方式。他在后记中说:“我在借雾霾表达我这一时段的心境:生活的确是尘雾弥漫、十面埋伏”。由此,社会现实的问题再一次回到了人心的问题。让人略感遗憾的是,这样的创作观念在小说中似乎体现得并不彻底,过多的巧合和字里行间的匠气,还是透露出作家描写现实的急切和过于强烈的吞吐万物的野心。《第七天》的教训就在眼前,小说不能仅仅是“匆匆忙忙地代表着中国”(张定浩语),从浮皮潦草的现实进入到宽广、驳杂、深邃的人心,这样的写作让人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