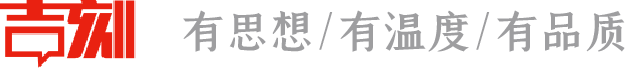编前语:11月20日晚,著名诗人曲有源去世,享年79岁。曲有源,吉林怀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新诗学会理事,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有诗集《爱的变奏》《句号里的爱情》《曲有源白话诗选》《曲有源绝句体白话诗集》《删繁就简》。诗歌《关于入党动机》获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1979-1980);2002年诗集《曲有源白话诗选》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24日,中国作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任林举发文悼念,回忆曲有源的“爱诗如命”,以及二人“以文学为桥,你来我往,一往而深,结下了一段情同父子的师生之谊”。

多年前,读老师曲有源的一首诗《水 在海里》,激活了我熄灭多年的文学热情,乘兴写了一篇品读文字。几经周折,被曲老师从一班耽于玩耍的文青中找到,拎了出来,并很认真地告诉我,人生还有另一条路可走。于是便以文学为桥,你来我往,一往而深,结下了一段情同父子的师生之谊。
老师一生爱诗如命,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用无力的手吃力地勾画着内心闪耀的诗意。在一张白纸上歪歪斜斜地写下:“诗的纪念碑已显现碑文。”去年春节前,老师癌病发作,我就知道我们此生的缘分快要尽了。为了留个念想,我决定在他浩如烟海的诗稿里选编一本我喜欢的,也是他自己认可的诗集。也许这是今生我能为老师做的他最喜欢的事情了。诗集的名字几经更改,最后还是按照我的意见叫做《水 在海里》,就是曾唤醒我文学神经的那首诗的题名。值得庆幸的是,在老师闭上眼睛之前终于看见了诗集的出版,而让人哀伤的是,就在诗集抵达老师的枕边时,他已经无法再检阅那些思想和心血的结晶体了。
一切的结局或结束都在人们的意料之内,似乎也在他自己的预感之中。在上海做完手术之后,他很快就知道了的自己的病情。但他是一个坚毅、刚强的人,从他当时的情绪和态度上判断,可以确定他是坦然接受的,并没有任何的紧张和恐惧。
有一天,他可能真的听到了死神的脚步正一点点逼近,开始以诗描述自己对生命或死亡的理解,用颤抖的笔迹写下一首叫《死亡定义》的短诗:“就是睡过去,再也叫不醒的那个人。”如今,他就是那个谁也叫不醒的人了。哪怕是千呼万唤,他也不再回头,如溪水直奔江河、江河直奔大海那样,断然而又决绝。
明天,老师就要在一场躲不过的烈火之中飞升到生命的必然归处,我却因某种不可抗力的原因被阻隔在另外一座城市,独坐灯前,凝视着他那张长发飞扬在风中眺望远方的照片,回忆往昔的点点滴滴。
遥想当年,他形象是多么强壮伟岸啊!虎背熊腰,健步如飞,蓄一头长发,披散着,因为长期承受日光的照射,脸呈现出古铜色泽,一双睿智的眼睛放射出坚毅的光芒。无论熟悉的人还是陌生的人,差不多一眼就能从他的神态中读出过往的坎坷与沧桑。常常,他穿着一件粗布的花格衬衫,背一个硕大的原牛皮背包,走在去南湖的路上,像赴一场生命之约,以肌体,以诗情去感知水的存在、水的路径和水的归宿。
当初读到他的诗句“水在海里,是什么地方也不需要再去的样子”,以为他已经彻底了悟人生,变成了海里的水,像他在诗中说的那样,尽管有时起伏有时摇荡,有时翻卷有时回旋,但种种状态最终都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安稳。
时至今日,再回首,不得不承认,我当初的认识确实还是有些肤浅、片面。实际上,他虽然在日常和社会生活中进入了一种不流不淌、无欲无求的安稳状态,他的灵魂、他的诗心,还在路上,远远没有到达安歇之处、安歇之时,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急切更加争分夺秒,甚至可以说,他已经决然放下一切,只为在诗歌的路上没有牵绊和阻碍地奔跑。
长期以来,他闭门谢客;杜绝了手机、电脑和外界交往;不参加任何文学活动;除了住院手术,每天坚持写三首诗,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一切都是为了诗,为了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全部利用起来,献给他钟情的诗。为了减少心脏的负担,他强迫自己做高强度的长跑训练,把90公斤的体重减到70公斤以下。为了降低血脂和血糖,他每天吃有限的食物,拒绝主食,副食少量,花生米十几粒、芝麻一汤匙、核桃一个……经过严苛的计算与“克扣”,他所摄入的能量基本接近生命极限,每天摄入的食物刚刚够写三首短诗,三首诗写完就得马上关闭思维系统进入睡眠。为了强健体魄,锻炼意志,他还连年坚持冬泳,将自己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之中……竟然在确定癌症晚期时,他还在说:“多亏发现得晚!”他的意思,如果发现得早他就有可能要早早进入治疗,没有时间来有条不紊地做手头的工作。其时,他正在整理编辑他的另一本诗集《删繁就简》。或有意或无意,他已经将自己推向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苦修之路,宛若诗的圣徒。
然而,偶有闲暇他也会食人间烟火,叫老伴儿或女儿打来电话,邀我去家中小坐。每次,总有他攒下的好酒,总有他最近写出的新诗,喝酒谈诗,谈他在新诗探索之路上的种种尝试,谈他对新诗热爱之余的某些理想。谈文化传统,谈诗歌技巧,谈语言的砺炼,谈文体间的贯通和互化,也谈如何吸纳众家之长。谈到最后,总是不忘对我教育、叮嘱一番,让我放下一切没有必要、没有意义的人事交往,排除那些没有意义且浪费时间的杂念和琐事,倾情、倾力、倾心,专注于文学创作,更教导我时刻保持足够的清醒和警惕,不要让自己的脚踩到自己的脚印,也不要浮躁、骄傲,双脚离开大地。
世纪之初,我刚刚完成了文学生涯第一篇像一点儿样子的作品《玉米大地》。完成初稿后,自己并不知道作品的成色如何,迫不及待地把稿子寄给老师。那时,他是吉林省唯一一个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正在厦门儿子那里居住,每天他要到海里游泳或海滩散步。
稿子寄出后我就在想,如果老师看过后否定了这部作品,我就得认真考虑自己是否适合走文学之路,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如果老师予以肯定,那我以后就要集中精力接着写,好好写。接到书稿后,他拿着稿子去了海滩,走着看,坐着看,走走停停,看看,从清晨傍晚,以一个具有三十几年素养、经验的老编辑的目光,对那部稚气尚存的作品进行了认真地审视。放下书稿,立即给我打来电话。那天具体说了哪些话,由于那时还年轻,过于兴奋,根本就没听清那些好听的话、鼓励的话具体是什么内容。但最紧要的一句却牢牢地记住了,一直记到如今。他说:“在中国,应该有这样一部作品。”现在回想,不管曲老师说这句话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对当时的我,无疑是一针能决定“文命”生死的强心剂。
不久,他又从厦门寄来一首特意为我写的诗,名为《枝枝向北》,诗不长,大约十几行,大概意思是借用武夷山上一棵枝叶朝北长的树的意向,传达出对北方对友人的思念。稍后,他又突然放弃了厦门回到吉林定居。朋友们欣喜之余,忍不住要问他为什么放弃山清水秀的厦门回到荒凉的北方。他的回答倒也简洁:“因为北方有我的根,有我的朋友。不管是否能天天看见,但我能感觉一伸手就能够得着……”一番话说得大家心热眼红,我却从此知道有些事情、有些人、有些心意值得我们备加珍惜。
遗憾的是,人性的麻木和懈怠常常让人在行走中忘记初衷和当初的信誓。让自己亲手描绘的生活蓝图被水渍或风雨侵蚀,失去原来的色泽和光彩,包括友情、亲情和容易散失的温暖。日子归于平静,大家各自忙于自己的事情,写诗的写诗,作文的作文,奔忙逐利的执着于四处奔忙逐利。因为总相信来日方长,每次与老师的相聚总是那么云淡风轻,不以为意。就这样风一样来,风一样去,却忘记或忽略了岁月如风,正悄无声息将我们的时日偷走,将生命的沙丘丝丝缕缕地搜刮、削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知不觉间逝去,我们都不再是从前的样子,老师的腰渐渐地弯了下去,体魄、体重、脸上的血色和意气风发的气息都渐渐从他的身上蒸发而去。老师老了。

2021年,曲有源寿宴上,任林举、曲有源、萧森。(从左至右)
某一年初冬,大约也是现在这个时节。熟悉的人民大街两侧高楼林立,夜晚的街道灯火通明,五光十色,大街上的车流拖着一条光的尾巴往来穿梭,将整条街道描绘成一条色彩的河流。
那个晚上,我和老师在他的家中秉烛长谈。也许是因为我有一本新书出版;也许是因为老师的新诗集即将付梓;也许是因为多年来的彼此相互关注、关心,以及那份与文学并无关联的情谊……我怀着无限感慨静静地聆听着他重复了多次的叮嘱,从生活到修身,从工作到文学,从现在到未来,从理想到信念……我深深地知道,那夜不同寻常,却不知室内温暖窗外寒冷,正有一场大雪在无边无际地飘落。
当我深夜离去时,老师执意要出门送我,并执意要站在大雪中陪我候车。雪花大朵大朵地落在他已经不再浓密的头发上,落在他已经微驼的背上和他表情凝重的脸上。瞬间,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苍老不堪。那情景,让我感觉我可能正面对一次隆重的远行。但我想得更多的是多年之后,回想起那晚雪中的情景,心中会涌起怎样的波澜。
多年后,果然又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纵然大雪依旧,街头也不再有曾经的故人。
这个冬天之后,老师将不再与我见面,他去了哪里,为什么一去不回?我手捧他那张神采飞扬的照片,端详了很久,终于悟出了一些玄机,或许,他是嫌这个世界能够理解他的人、懂得他的人太少,他要去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寻找知音,以至于那么多的朋友和亲人都拢不齐能够挽住他的力量;或许,我这个自称为他学生的人,从来也不够优秀,根本就不值得他浪费心思和情感,他要将一些隐秘的夙愿托付给另外更加值得的人。或许,他来这个世界就是要完成自己的一个使命,事情圆满之后,匆匆留下一句“诗的纪念碑已显现碑文”,就转身离去。
是的,我们从来没有透彻地明白他的本意,包括他的话语、他的那些诗句。他不是早已经告诉过我们吗?水在海里。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并没有强调时态。现在重读,他的意思却是,水,将在海里,要归于大海。海是水的归宿,水的天堂。我终于明白,时至今日,他的生命之水,他自强不息的灵魂才真正抵达了那个浩瀚无际的大海,进入他最本真的安稳,就是安息!那就安息吧,我的老师,我们今生就此别过!
来源:中国吉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