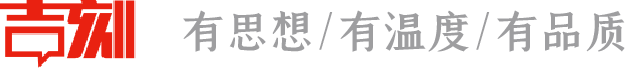《水 在海里》 曲有源 著 任林举 选编
使命有时由他者赋予,有时由自己赋予。对于庸常的人来说,使命即是重负,是一种与人的本意、本性相背离的事情,并没有太多的人愿意把使命扛在自己的肩上。既然如此,为什么人群中偏偏要有人肩负使命并至死不渝地忠于和恪守呢?有一些很好理解,因为群体和自身的现实需求,为了声名和利益也要扛着;而有一些并不好理解,似乎没有人需要,也没有明确的名利可言,一切都缘于自身某种隐秘的意愿或某种难以追查的原因。既然不好理解,按照人类一向的做法,就会将这些不好理解的原因归结为天意好了,认为是上天将某项有现实意义或没有现实意义的使命赋予了一部分人。
自从认识诗人曲有源的那天起,我就感觉到他是一个肩负某种使命的人。他写诗,是中国著名的诗人。他一生的衣食和甘苦都因诗而起,早年,他在一个小城的兽医站工作时就开始爱诗、写诗,后来因为诗的缘故,他的名气渐大,得以从小城迁居到省城,谋生的职业也从给各种禽畜看病的兽医变成了给各种文章也包括诗歌看病的编辑。当然,在给别人修改和编辑文稿、诗歌时,他也没有放弃过诗人的本份,自己也在孜孜不倦地创作自认为完美的诗歌。编辑和诗人,是他一生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也是他最后的头衔和称谓。
然而,仅凭这些还难称什么使命。我们这个时代,编辑只是一个职业,称职的和不称职的都可以充任,图书市场这么大,人们的阅读需求又那么复杂、多样,多一个编辑,也不见得就能改变了一个时代的写作或阅读风气,少一个编辑,也不会让任何读者感觉到缺少点什么。论及诗人那就更不用多说了,人们早就把阅读的目光和心境集中于商业传奇、致富神话、网文和微信、抖音上了,连纯文学的小说和散文等都已经被人们弃之如敝履,更何况文得雅得难懂的诗了!“饿死诗人”的说法,已经在岁月的流程里延宕了不止十年八年的时间,诗人只在文学圈子里还算正常的人类,在普罗大众的眼中,恐怕已经成为行为、思维都很怪异的另类。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曲有源突发奇想或打定主意、立下志向,去拯救处于颓势的汉语诗,特别是新诗运动以来的白话诗。他要把白话诗写成既深刻易懂又短小精悍、人人喜爱的新经典。是的,这就是他的使命。如果他不是把这件事情当做一项必须完成的使命,他就没有必要将生命的全部毫无保留地投入到这一件事情上来。应该说,曲有源所肩负的使命完全与别人无关,既没有组织委托、群体意愿相加,更没有临危受命,是他自己加给自己的。为了完成他心中的白话诗经典,他甚至不惜付出需要付出的一切,包括他应该得到的鲜花、掌声、热闹、舒适、娱乐、享受,甚至健康,甚至自由。直到80岁高龄,他还要保持着每天创作和整理三首诗的节奏,除了住院手术期间有短暂的间断,其余的时间基本雷打不动。对诗的创作与推敲已成为他生命里最为重要的事情,毫不夸张地说,其重要性仅仅次于呼吸,只要他的意识清晰,他脑子里想的就是他的诗。
他这种近于痴迷或者疯狂的状态常常让我担忧。我担忧的,并不是他的投入和收效之间会不会获得一个合情合理的平衡,而是他生命中的能量会不会如蜡炬燃烧一样迅速耗散。但我的担忧似乎多此一举,因为无论在诗歌技艺上和身体条件上,他都心知肚明,似乎也有充分的准备。他所作的一切看起来都不是随意的、盲目的,而是精心策划的和有序实施的。他试图自己掌控自己的生命节奏和命运,他似乎也很自信一切他都能够把握得很好。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他曾经两度获得的中国最高诗歌奖或许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些年,虽然他自己从不提及,但所有关注中国新诗的人们都还清晰地记得他那两次耀人眼目的辉煌,一次是全国诗歌奖,这个奖正是鲁迅文学奖的前身;另一次则是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哪一次都不是浪得虚名。
他尝试将白话诗写成唐诗和诗经那样的经典,是在他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后的事情。这个时候,他的名和他的利都已经在现实中得以实现,他不再需要为生命中那些低层面的需求而拼命。如果继续拼下去,也只能是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或难以名状的使命。
曲有源在中国诗坛上成名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从1994年开始,他潜心从事“白话诗”的写作。我理解,所谓白话,是有口语和书面语之分的,诗歌界所强调的白话诗,实际上就是用口语入诗。当前被一再强调的民间立场,其要点无非有二,一是口语入诗,一是突出非主流意识。其实口语入诗说明不了什么,口语入诗不过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相反大量没有立意没有灵魂的口语诗的出现,正是所谓“唾沫诗”产生的直接根源。其实,非主流意识也都说明不了什么,不过是有意秀一秀自己的“倔性”和特立独行,充其量不过是一己小个性,本来存在也没什么不对和不好,但特意去强调并摆出压倒一切的姿态就有一些画地为牢的偏执和偏狭。在这里,我是说曲有源最独特的地方并不在于采用口语写诗这一点上,而是他在“白”的形式下,始终自觉地坚持了他独特的诗歌立场,同时对西方技巧、古典意韵的兼收并蓄,将诗写得平实、明白且隽永、深厚,做到了本质上的不“白”。
1995年秋天,曲有源参加了四川阆中一个全国知名诗人的聚会,会议期间他从古城阆中到九寨沟,再到剑门关,一路感悟,一路思索,一路行吟,写下了著名的组诗《白话说诗或发挥暗喻》。这个很不像诗题的题目,包含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白话,一个是暗喻。这组诗饱含了他以最新的感悟和最新理念结构而成的30首面貌一新的诗歌。我理解,这是他诗歌创作的一次小小的爆发,也是他以诗说理以诗阐释他诗歌主张的一个宣言。今日重读当时的那组诗歌,仍能够激发出很深的内心感触。在此,不妨选录几首。
成都明清茶楼速写
——听琵琶曲 《阳春白雪》之后
冬天的冰尚且很难
留存下来
这阳春的白雪
焉能不铮铮而成
两弦之间的柔波 这月儿
还是二泉里曾经映过的
那轮月儿
此刻颤抖成
竹编罩里的灯影
夜 毕竟很深了
穿印花蓝旗袍的仿古小姐
也许因为
手太瘦太小
掩不住百年前就来了的
一个
元末清初的哈欠
羊走在羊肠小道上
山羊
把自己的羊肠
用羊皮裹紧
像一粒粒褐色的麦粒
移动在大山的
羊肠小道上
后面的牧者
似乎不知道
世界上除羊叫以外
还有什么
语言
废弃的水磨
用最后的生机
绽出老年斑似的绿苔
以此伪饰 说明
自己还算年青
这有什么意义 如果
曾用温柔的缠绕
使你兴奋起来的水流
一去不返
而你渴望的上游
早已从源头
改道而去
显然,几首诗都是纯粹的“白话”成诗,就语言表意上说,没有一个生涩难解的“古”“雅”字、词,平白如话,但组合起来却远远超离了其字面意义,并且其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几何级别的放大。经过诗的点化,“哈欠”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女子口中的哈欠;羊也不再是山路上觅食的羊;水磨也不是那个没有气息没有思想的死物了。
中国的新诗,尽管来自于西方的诗歌传统,但实质上,无论如何都抹不掉其中国文学的基因,至少无法否认汉语的传统。就拿欧美诗歌传统中的意象为例吧!是抛开本体语言释义影射、指向更多释义的物象。其最著名的诗句就是庞德的《在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庞闪现/ 湿漉的黑树干上的花瓣”这种诗歌主张,作者自己的解释是:“一个意象的诗,是一个叠加形式,即一个概念叠在另一个概念之上。”如此一来,甚嚣尘上的“断裂”之说是不是就现出自相矛盾的尴尬啦?其实,在一些诗歌的运用过程中,意象和暗喻在修辞果效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回过头来,我们再去中国文学传统和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对应,则会发现,同样的技法或修辞则比比皆是。流行于民间的指桑骂槐,桑与槐,既是概念的叠加或互相替代,也是一种暗喻。再说古典文学中的那些咏物诗,应用的几乎全部是意象或暗喻的技巧,只不过当时并没有人给这个技法起一个洋名。比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比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是具体的实物吗?显然不是!如果说,所谓的意象,是物与物的相互指代,那么古诗词中的意境则是物象与心境或境界的相互指代,从技巧或手法而言,两者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和感悟,曲有源毅然走上了背叛之背叛的新诗之路,他要从热闹一时的“新思潮”中超越出来,反身回归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借助古今中外的诗歌精髓为拒绝意义、反叛传统的中国新诗找到本真的源泉和灵魂。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间,他重温中国古典诗词,博览国内外新歌经典之作,包括欧美、台湾以及海外华人的诗作,同时也进入到其他文学艺术门类以及广博、幽深的民间,熟谙各种诗歌技巧和覆盖世界的语言智慧,探索出一条回归经典,向经典致敬和打造新诗经典的诗歌创作之路。如果说1995年秋天的那组诗歌《白话说诗或发挥暗喻》是他最初的宣告,那么后来的20多年则是他在新诗发展之路上的深刻实践,并将隐喻在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发挥到了极致,当然,也成功地创造了某种意义上的新诗经典。
2000年,正好是世纪之交。曲有源以一本《曲有源白话诗选》荣获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登上了中国诗歌的宝塔之端。在这本诗集里,曲有源娴熟利用各种诗歌技巧,包括隐喻,包括“移花接木”,包括“词语破壁”等他自己探索出来的诗歌技巧,完成了他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将诗写精,写深,写大。在一些诗歌里,他以“刚性的”、固定不变的、不生歧义的如常用语在他的诗歌熔炉里完成了化合反应。总之,就是通过对词语的遴选、打磨、组合,剪裁也好,嫁接也好,转基因也好,催生出一系列“物理”的或“化学的”变化,将一些具有坚固外壳的词语,去其硬皮,剥离表意,透出隐藏于内的亮色,使意义和意味得以深化和放大,使诗意或者诗意以外的意味像树木新鲜的汁液一样,像从金石的茬口中闪射出诱人的光泽,照亮我们的双眼及灵魂。这就是诗艺,也是诗歌的秘密。此时,这一切都被曲有源稳稳地握在手中。现在,我们来品读一下这两首短诗:
猝死
一个朋友惨叫一声
死了
嘴半张着
现场还留在胸膛
腕上的手表里有脚步声
秒针像寻找出口的逃犯
即便是
为什么那么干净
即便是她额上的皱纹
是一块遗忘的
搓衣板
而往事
这件脱不下去的内衣
我又不曾
去洗过
诗写得很短,意味却格外深长。同样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词语,但在诗人的精心组织下,却释放出了震撼人心的能量。在《猝死》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谋杀”,诗人还让我们看到了那个隐形的杀手正是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握于股掌之间的时间,更可怕的是,它无处不在,让我们无法逃脱。而在《即便是》中,却深刻地揭示了最终使往事成为空白,使我们的心及行囊空空如也的,正是来自我们自己的遗忘。曲有源的诗往往都是这样,精短、空灵、深邃、不动声色却又如撕心裂肺,情感浅淡却又似深如潭渊,这就叫格局。他总是从低处出发,从细节出发,从自身的生活出发,然后超离,将自己的痛痒转移为普罗大众的痛痒,将自己的小情感转化为人类的大情感,将囿于红尘俗世的小视野放大为天际、云端的大视野。于是,经过冲淡、虚化和升华,那些浓得化不开的小情感、剧烈得不吐不快的小感觉,遂升腾为关于人类,关于生命,关于大地、天空和宇宙的大情怀。
曲有源这一时期的诗另一个特点是,在形式和取义上实现了与古典诗词的靠近或接轨。很多诗都巧妙地借用古典诗词或成语语汇,用现代人的观念、情绪加以关照,使其生发出奇异的光辉。如:岁月采我时是不需要东篱的/而那神态/我相信/肯定要比有山可望/还悠然……(《岁月采我》) ;看来/春到南宋时/就很浅了……及到我来杨州/在二十四桥的草地上/发现一片/早夭的叶子/我竟未敢掀动/怕揭开来/下面就是/很深很深的秋了(《春浅》)。但他这个时期的诗歌是自由的,还没有如古典诗词那样具有固定的形式。诗歌形式基本是这样的:
话到舌尖
挥手而去的离人
是被说出去的话
不知流落何方
莫非后悔食言
天和地紧抿成
一条地平线
想冲口而出
又有所顾忌
我是话到舌尖而被留下的
那半句
然而,一个诗人或一本诗集能否获奖终究是一件身外的事情,是外界或诗坛对他的承认或确认,而不是他对自己的态度和评价。于他自己而言,虽然鲁迅文学奖这个荣誉足够高大,以庸俗的想法,也足够他把老本吃到终老,但他自己却并没有因此而满足、驻足不前,他认为,自己的诗还没有达到经典的高度,不论内涵、技巧还是诗歌形式,都需要有一个超越性的提高。这时,他想到了古典诗词的语言密度、境界的高度和令人赞叹的规整和精巧。他认为,新的经典,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更精、更短、更整齐,密度更大,意境更加深远。所以,从这个阶段开始,他明确给自己提出了“绝句体白话诗”的概念或目标,在打造经典的里程上更进一步。
对此,他自己做了如下阐释:“ 有史以来,诗体的演变是循序渐进的,是基因的慢慢转化,不论由诗到词,还是由诗词到小令。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诗对古体的断裂之举,导致它和传统的脱臼、脱轨,以至于出现现在人们所熟视的局面。我在十多年前开始演练的白话诗,如今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早已被摒弃的起承转合,居然在操作过程中,借诗还魂。它不是凭空设计的新诗格律,而是在实践里,与汉语内在规律的磨合,恰如齿轮散乱后的复位,如经典相声小品的打造,追求语言的水到渠成、精益求精。而相比之下,那些有起无承、有承无转、有转无合之作,似乎属于写作的初级程度……”
在曲有源的诗作之中,有一首《水中的尘埃》,最能体现他那个时期的心境和生命状态。
水中的尘埃
在远离甚嚣的地方
它甘心于
比落定
还低的地位
连浑浊
都是缤纷的回忆
说起归宿
这何尝不是
最静的一种
它甚至都不想
在浮力的支持下
去做一次
泛起的努力
这又是一个“发挥隐喻”的成功案例。因为尘埃落定是一个成语,而落定之物定是指涉了尘埃,它落定的地方是地平面,于是我们便想到落到地平面上的尘埃是比水中的尘埃还要高一些,也就是水中的尘埃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低到已经没有人把它当做尘埃了。这里面又是一层深意。落到水中的尘埃为什么平常并没有把它看作尘埃呢?因为它已经得到了水的净化,因为它已经获得了完全不同于尘埃的重量。甘心于比落定的还低的位置,之于尘埃,它是一种状态,之于一个历经沧桑的人,这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很自觉的人生境界。人生,到了一定的境界真是静啊,就连当初的浑浊都是一种缤纷的回忆。到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诗人的心是平静的,对于过往的恩怨,对于过往的爱恨情愁、喧哗热闹,他的态度是既不迷恋,也不愧悔。不迷恋就没有那些怅然若失,不愧悔,就没有了那些痛彻心肺。
心如止水,我想就是这个样子吧。古代的圣人在说水时是这样说的: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那么,曲有源究竟在潜心修的什么道呢?隐喻之道,诗歌的淬炼之道!
古人写诗写得苦,特别是唐宋时期的诗人,要么“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要么“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非要在区区几十个字里营造出大境界、大乾坤来。曲有源认为,那个时代的诗之所以写得“绝”,并有很多成为了不可巅覆的经典,正是那个时代的诗人能够把诗当做千秋万代的事业,不但肯用功,而且肯用命。为了打造他心里的现代诗歌经典,曲有源肯把自己的生活和生命都调整到符合诗的要求。
25年以来,他闭门谢客;杜绝了手机、电脑和外界交往;不参加任何文学活动;除了住院手术,每天坚持写三首诗,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他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全部利用起来,献给他钟情的诗。在这样做之前,他思考了很多相关的事情,他估计到要想把这件事做好,自己的时间很有可能不够用。他心里清楚,他要做的事情可能需要几代人前仆后继才能完成,但从眼前看,只有他自己能够全力以赴。为了完成他自己的使命或者给后来人打下良好基础,他就得想尽办法为自己多争取一些时间。除了要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在诗上,另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加自己拥有的绝对时间,尽可能地延长生命。为了减少心脏的负担,他强迫自己做高强度的长跑训练,把90公斤的体重减到70公斤以下。为了降低血脂和血糖,他每天吃有限的食物,拒绝主食,副食少量,花生米十几粒、芝麻一汤匙、核桃一个……经过严苛的计算与“克扣”,他所摄入的能量基本接近生命极限,每天摄入的食物刚刚够写三首短诗,三首诗写完就得马上关闭思维系统进入睡眠。为了强健体魄,锻炼意志,他还连年坚持冬泳,将自己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之中……他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推向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苦修之路,他是诗的圣徒。
至于诗,当然也被他精简到没有一字冗余,并且还要遵循某种固定的排列。尽管这一时期的诗歌形式在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层面接受度并不高,但在诗的内在质地、语言、意境等方面还是成熟的、精到的和不容置疑的。诗人自己也曾以各种渠道和各种方式表示,由于在这些诗歌中,自觉地继承了传统诗歌短小、规范、凝炼的外部形式和起、承、转、合的构建机理,同时加载了高密度的东方智性和个体上的性灵以及艺术方法等要素,使诗在与文学传统对接以及与本土文化融汇过程中,重新获得了神秘的力量。诗人这一时期的诗歌,形式感很强,差不多都如以下这首诗的样子。
经历
一页橡皮走白的白纸
一片被鸟儿的翅膀
移动过来的天空
一个从墓穴里
出土的骨笛
一片蛙鼓
震颤的
水面
一
个
长吁
短叹后
废墟上面
遗弃的烟囱
一棵风领不走
叶落不归根的树
一扇被手敲过的门
一个他被她她过的他
面对这样一批外表整整齐齐的诗,曲有源曾自己将自己称为诗匠。我倒是觉得,匠心是有的,但和一般意义上的匠,还是不同的。一般的匠,只有工艺和样子而没有创造,而曲有源的所有诗都是独具匠心的创造。他的自谦恰恰体现了他的冷静和自觉。
客观地说,曲有源的诗之所以能够达到现在的高度,惟一能够更加接近本质的表述则是:长期修炼的结果。除了修炼,没有什么能够对他长期以来在白话诗领域所做的试验、探索和磨练进行命名。他知道诗并不是套用一两个现成的理论、与哪一个师傅学上三招两式或耍一耍小聪明,偷个机取个巧就能成就的,所以他把北方人的幽默和智慧、语言的特色、人生的经验、生命的感悟、汉语传统中的精华、汉语言文学中经典的表现手法、现代人的思维、意识和人类共同的思想、观念以及当时的生命状态、心境搅到了一起,进行了一场殚精竭虑的冶炼。
转眼又是十年,当时间进入2021年的春天,诗人已经进入80岁的边缘,因为长年的节食、劳累和渐渐入侵到肌体中的疾病,他的体重已经减少到了60公斤,原来挺直的腰身也渐渐弯曲了下去。曾经一度对他宽容、退让的岁月,已经转身来敲他的门,向他索要旧日的欠账。这时,他也露出了从来没有的倦容,他太累了。但他还是坚持从堆积如山的诗稿中抬起头来,说了他对诗最后的感悟和坚持:“删繁就简”。再度阅读他的诗,已然是另一种样子,原有的形式不见了,但却变得更加精炼,更加轻盈,如突破茧的束缚,一跃凌空因风而舞的蝶。随便录两首在这里吧!
石头
石头之所以那么沉重
因为它
包含世界
所有的形象
只要你雕塑时
能剔除多余的部分
螺丝钉的决绝
螺丝钉的决绝
世上少有
为了坚定不移
只保留一个脚尖
又把自己
一生该走的路
都缠在身上
确实已删繁就简了,正如他在那首《风的成长》中所写的那样:“春风浪漫的时刻/是在万紫千红里/走马观花//他的成熟也在秋天/所到之处/都能删繁就简”。这风,正是诗人思想的风,也是他多年来对诗的认识和感悟。删繁就简,不仅让我想到了他的诗,也想到了他的生命和生活。秋风过后,是另一个季节,一切,包括风,都将停歇下来,因为在树叶都不剩一个的北方冬天,已经没有什么能够进一步删减的了。
粗略地算一算,在25年的时间里他写出的新诗至少有两万多首。现在他要对自己的一生追求有个交待,他同意了我要从他这两万多首诗作里遴选出300首集中展示的请求,以此作为他诗歌成果的一个小结,也作为向唐诗、宋词300首的致敬,更给后来人借鉴或评说留一份依据。时已至此,他也该歇一歇喘口气啦!毕竟,作为一个诗人,他应该做的一切都尽力做了。无论结果如何,他完全可以自豪地对自己说,此生并不虚妄。他已经对得起顶在头上那个著名诗人的名号了。
本文选自时代文艺出版社《水 在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