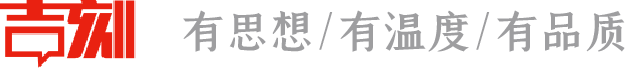西阴村位于山西运城市夏县,是一个别说在中国地图、山西地图,就是运城地图上都不可能标注的小村落,但是这个小村落却在每一个中国考古人心中有着沉甸甸的分量。1926年,李济先生主持的西阴村遗址发掘是中国人主持现代考古发掘工作的开端。这一步的迈出,实现了前贤先哲们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古今对话,开始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认知开端。用考古大家张忠培先生的话说:“1926年10月15日,李济先生踏入西阴村遗址,定好基点,布方,接着挖起第一锹土的时候,这短暂的一刻成为历史的永恒。”
疑古与信古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于一切旧事物都持怀疑态度”的思想开始在学术界生发。中国历史学也受到深刻影响,进而诞生了一个学术新流派——疑古派。这个学派的宗旨就是运用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疑古辨伪,揭示有关中国上古史记载的真面目。其中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顾先生的这个观点主要内容有: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譬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出现三皇,汉以后才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顾先生形成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正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譬如,我们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顾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这就形成了自三皇以至夏商,都无信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传统的上古史被推翻,破了该如何立呢?
1899年,有深厚金石学修养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然发现了甲骨文。王懿荣殁后,他的好友刘鹗以及刘鹗的亲家罗振玉也相继开始收购研究甲骨。罗振玉除了研究,还派其弟罗振长前往安阳调查,弄清了有字甲骨的出土地是安阳小屯附近。甲骨文的发现,引起了学界的重视。王国维进行深入研究后,于1917年接连发表《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等著名的“二考一论”。他通过考证研究,发现《史记·商本纪》中记载的商王世系竟与甲骨文材料相对应,这就说明《史记》的记载是可信的,我们信史被重新“找回”了一千年。学界之人看到了地下实物与传世遗文相互印证的问学新路。“地下材料”的寻找越来越引起重视,“考古学”即将走进中国。
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考古这个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北宋蓝田吕大临所辑的《考古图》一书中。19世纪末,西方舶来现代考古学这一学科。对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首倡之功的是瑞典人安特生。安特生1901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1914年被北洋政府聘为农商部顾问。他领导了1921年秋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安特生是第一
个在中国古文物调查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而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由谁完成呢?历史的责任落到了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也就是后来被尊称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肩上。
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北钟祥人。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随即被派往美国留学。曾在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1920年入哈佛大学,1923年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当年回国后,李济先生执教于南开大学,1925年重返清华园,执教于鼎鼎有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
李济先生于1928年10月又出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此后相继主持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掘,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则是他主持田野考古的开端。李济先生迈出的这一步,是中国人首次主持田野考古,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也奠定了李济先生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地位。
偶然发现的西阴遗址
在疑古与信古的大背景下,经过王国维等大师的研究,商代的历史被地下出土材料印证是真实存在的,那同样是《史记》中记载的夏代呢?这也是当时李济先生考虑的问题。夏朝的中心在哪里呢?文献记载是在山西南部夏县一带。基于此,才有了他1926年的晋南调查。
出发前,他们做了充足的准备,请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以校长的名义给山西省长阎锡山写了介绍信,还结伴中国地质调查所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同行。袁先生具有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曾参与过安特生1921年的仰韶遗址发掘。他们于1926年2月5日从北京出发,那一天是农历的小年。在2月7日到达太原,15日到达绵山,25日到达临汾,3月22日到达夏县。李济先生在他的《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一书中记述道:“夏县——传说中夏朝王都。据传大禹庙以及禹王后裔和许多著名大臣的陵墓都在这里。所以我们去寻访了。不过说实在的,从外表上判断,我根本无法肯定这些都是或者不是真正的陵墓。它们看起来都像是普通的坟冢,只是稍大一些。可是,在我们寻访这些陵墓的途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当我们随意捡拾一些暴露在地表的陶碎片时,聚拢了不少村民。我们没能在这里逗留多久,以免引起过多注意。”虽然他们在西阴村遗址逗留的时间不长,但还是收集了86枚陶片。这次调查是中国人自己主持我国考古发掘的先声,这处遗址在不久后也成为中国人自己主持田野考古的起点。
李济先生后来曾谈到为何选择发掘西阴村遗址。“我们这样选择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史前遗址不含任何金属品,可以避免挖宝的怀疑。二是发掘过去不知名的埋藏,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三是仰韶文化的发现,已排除了对史前文化重要性的怀疑。”除了上述原因,夏县传称夏墟,在此发掘与李济先生最初寻找夏代的设想也有一定联系。
1926年10月,李济和袁复礼等先生再次来到夏县西阴村,10月15日,西阴村遗址正式开始发掘,地点在现在的西阴村北。这次发掘耗时近两个月。在发掘中,李济先生创造性地使用了探方发掘法,这样便于控制和观察下挖的叠压地层剖面。他们用层叠法记载一切看见的物件。由起点下行第一公尺叫A层,第二公尺叫B层,依次递降,用英文大写字母做标记。每一大层又分好多小层,用英文小写字母表示。他们还发明了“三点记载法”,就是把探方的东西向叫X线,南北向叫Y线,下挖的深度(即下行线)叫Z线。以今天的眼光看当时所做的工作,不能说是完美的,但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如探方发掘法、三点记载法(即三维坐标记录)、按层位采集陶片等方法,直到今天我们在田野考古发掘中仍在使用。所以说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对于中国现代考古学来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
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收获很大。1927年初,他们把发掘出的遗物及物资装了几十箱,雇了9辆骡马大车,从夏县拉到榆次火车站,再转火车到北京。夏县到榆次他们走了9天,在运输途中,沿途百姓看着两个年轻人和一个车队,车上箱子里装的东西沉重,以为是什么宝贝。到了榆次火车站时,被官方截住,开箱检查。结果开一箱是“破烂”陶片,下一箱还是,第三箱又是。往北京运送这些“破烂”,检查人员觉得奇怪又无语。他们不懂也正常,因为这是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的收获。考古,在当时还不为公众所认知。
半个蚕茧和石雕蚕蛹
李济先生发掘的西阴村遗址资料早已公布,影响深远。这批发掘材料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出土了半个6000年前的蚕茧。李济先生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描述:“我们最有趣的是发现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看,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极平直。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
这半个蚕茧无疑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李济先生对其极为重视。上面已经提到他回清华后请生物学家刘崇乐教授把关,1928年访问美国时,他又把蚕茧带去请华盛顿史密斯研究院的专家进行鉴定,其结论也是肯定的。但还是有学者怀疑其可靠性,理由是6000年前的蚕茧保存至今除非有特殊的条件。李济先生也一直比较谨慎,虽然在他的若干部著作中都提到这枚蚕茧,也提出了几点推论和思考方向,但并未下肯定的结论。那半个蚕茧从最初陈列于清华大学考古陈列室,后移交“中央研究院”,再归“中央博物院”保存,最后迁台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几十年来,该标本基本深居恒温恒湿的库房,唯恐出现意外,展出的展品都用复制品代替。
时间到了2019年,还是夏县,西阴村遗址南去十余公里的师村遗址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进行发掘。他们在仰韶早期的灰坑中,出土了多枚石雕、陶雕蚕蛹。据相关报道,“石头是当地中条山产的花岗岩,造型精美逼真,头尾清晰。师村遗址发现的仰韶早期石雕和陶雕蚕蛹及其共生的文化属性显示,距今6000年以前,地处黄河中游的运城盆地先民们已经了解、喜爱并崇尚桑蚕。”新发现接踵而来,2022年6月,西阴村遗址西去十余公里的闻喜上郭遗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又从一座仰韶晚期早段的房址中发掘出了一枚石雕蚕蛹。这些发掘成果公布后,很多人都联想到了李济先生在西阴村遗址发掘的那半个蚕茧。这些新发现,用考古学者田建文先生的话说:“(这些石雕蚕蛹的发现)说明山西南部涑水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养蚕,而且蚕蛹、蚕茧传承有序,也坐实了西阴遗址蚕茧的可信度。”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争论,随着不断出土的新发现,也该结束了。当地政府已然立起以李济先生发掘的半个蚕茧为原型的雕塑,这是对当地悠久历史的宣传,也是对李济先生功绩的肯定。
李济先生主持的西阴村遗址考古发掘至今已过了近百年。如今的华夏大地,已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前辈的事迹,或如他发掘的陶片,埋藏多年,早已残破零碎。但这些零碎事迹一旦拼合起来,则会让人感叹其伟大,回味其情怀。李济先生和他的西阴村遗址发掘,应该让每一位考古人甚至每一位中国人记住,并流传永远。(刘文涛)
来源: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