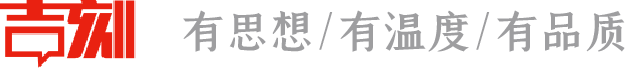壹 打牲乌拉
在与长春市九台区隔江相对的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曾经存在一个专为清廷采捕贡品的机构,叫“打牲乌拉总管衙门”。
“打牲乌拉”来源于满语“布特哈乌拉”。“乌拉”即汉语的“江河”,“布特哈”意思是“渔猎”“打牲”,所以“布特哈乌拉”也叫“打牲乌拉”,为“江河渔猎”“江河打牲”之意。
明代的东北,有海西女真的“扈伦四部”,其中之一乌拉部(亦称“乌拉国”)地域广大,明末时其王城便设在今乌拉街。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率领建州女真灭掉了乌拉部。
此后,努尔哈赤和诸贝勒每年派人前往乌拉地方打牲,各旗主也派出旗下包衣到那里采捕各自需要的人参、松子、貂皮等,乌拉地方成为后金的采捕基地。皇太极继位后,于天聪三年(1629年)派纳殷城的旗人之后——迈图来到乌拉,在旧城设置“乌拉地间嘎善”(乡村机构),迈图为嘎善达(乡村长),加强了对乌拉地方的管理。
随着乌拉地方“生齿日繁,地方辽阔,以嘎善达不堪镇服”,于是赏给迈图“满洲缺分,为内务府包衣按班三旗佐领”。为控制乌拉地方打牲的混乱局面,清廷于顺治七年(1650年)停止了宗室和各旗分别采捕东珠、貂鼠等物的惯例,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将迈图任命为总管,统一管理各旗派到这里的打牲丁,为清廷及各旗王公采集、保管、加工、输送贡品,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由此诞生。
从设立到宣统三年(1911年)撤销,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共存在254年,几与清王朝共始终。在这二百多年中,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非常稳定,名称也未曾改变,只在来往公文中会使用简称“打牲衙门”或“乌拉衙门”,总管也时称“打牲总管”。衙门初设时隶属清陪都盛京内务府,后改隶北京内务府。康熙年间,宁古塔将军迁至打牲衙门东南面的船厂之地后,打牲总管职务曾由宁古塔将军兼理过,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宁古塔将军卸去兼理总管的其他事务,只兼理采珠、捕鱼、拣选官员三事。打牲总管初放时为六品,随着事务越来越多,到康熙年间已升为三品,比同为清廷贡品基地的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衙门总管的品级高。
既然是为清廷采捕贡品的基地,打牲衙门就要有一个采捕区域,这就是清廷为其划定的贡山、贡江和采珠河口等。打牲衙门贡品的品种和数量不断变化,采捕区域也并不固定,至光绪年间已发展到“南至松花江上游、长白山阴,北至三姓、黑龙江、瑷珲,东至宁古塔、珲春、牡丹江流域。上下数千里,流派数百支”,涵盖了东北的大片山河。成书于光绪年间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记载,打牲衙门在这片区域内领有22处采贡山场、64处采珠河口和5处种粮官庄。
在采捕区域内,还有一个“不与驻防衙门干预”、由打牲衙门直接管辖、供打牲兵丁驻防和生活的专有区域,最大时边界如下:东以拉林河为界;西至煤窑厂(位于今长春市九台区);南由横道河子(位于今桦甸市)起至磨盘山(位于今磐石市)止;北面大致止于柳条边,沿松花江周围方圆300多公里。
打牲衙门的打牲丁最初不过几百人,后将本处各旗打牲丁后裔及发遣至此的人犯奏准入册,到康熙年间增至2000多人,以后最多时近4000人。宁古塔将军移驻船厂后,于乾隆年间在乌拉街地方添设协领衙门,领1000多名八旗官兵,平时归打牲总管使用,与打牲丁一同采捕,外有战事时归吉林将军(乾隆二十二年宁古塔将军改称“吉林将军”)调用。两处合计有5000多名打牲丁,可见乌拉之地打牲队伍的庞大。
贰 占地打牲
200多年来,打牲衙门为清廷采捕的贡品种类繁多,但始终采贡的有4宗:东珠、鳇鱼、蜂蜜、松子。鳇鱼,是仅次于东珠的重要贡品。
鳇鱼,学名达氏鳇,为冷水鱼,主要产于黑龙江水域,体圆,长可达四五米,重可达几百公斤,乌苏里江、松花江下游均有分布,春夏时节溯松花江而上,可达今农安、德惠江段,是东北的珍贵鱼种。鳇鱼肉鲜味美,在历史上曾是东北少数民族进献给中原政权的贡品,更是女真人祭祖和食用的必备品。
因为鳇鱼与同纲目的鲟鱼形态相似、习性相近,区分起来比较麻烦,古人便将这两种鱼统称为“鲟鳇鱼”。乾隆帝东巡吉林时曾作诗咏之:“有目鳏而小,无鳞巨且修。鼻如矜翕戟,头似戴兜鍪。”
打牲衙门向清廷岁贡鳇鱼的数量和尺寸,最初无定额,“尽所得呈交”。后来,“鳇鱼贡”的数目和尺寸有了定额,未足额便要受罚,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打牲总管索柱就因为所贡鳇鱼太小而被革职。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为鳇鱼生长期长、成熟期晚,捕获的成鱼渐少,便只规定每年进鲟鳇鱼20尾,不拘尺寸了。
鳇鱼作为打牲衙门采捕的重要方物,身形大,不易捕获,因此,打牲衙门从康熙五年(1666年)起,在打牲八旗上三旗中增设捕鱼珠轩(即作业组)6个,专门负责采捕鳇鱼等。几年后在下五旗内也增设了捕鱼珠轩,并在八旗中各增设领催一名,专领捕鱼。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左右,打牲衙门正式形成了独立于采珠八旗之外的捕鱼八旗,负责全部鱼贡。
打牲衙门开署以后,松花江是其最重要的采捕贡江,主要是采珠和捕鱼。但是,捕贡江段最初主要在柳条边内,由打牲衙门所在江段往上至横道河子、长白山阴,即松花江的“上掌”。乾隆年间,捕贡江段才扩延到柳条边外,即松花江的“下江”,原因是当时松花江“上掌”边里地区人烟稠密,水浅鱼稀,欲捕获更多的贡鱼,特别是大型鳇鱼、鳟鱼等,就必须到下游去。于是,为了方便打牲丁到边外松花江更远的江面上捕鱼,以及就近休息,经吉林将军同意,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打牲衙门将打牲用地范围扩大到柳条边外,即今德惠市松花江段,前后经过两次扩延。当时,柳条边外的松花江两岸都是蒙古王公所属的荒原,今德惠市鳇鱼岛在出边不远的松花江上,打牲衙门虽然可以在这一江段捕贡,但江上岛屿和两岸土地并不归其所有。
打牲衙门在第一次向柳条边外扩延时,“由伯都讷地方巴彦鄂佛罗边门外自饮牛坑起,至松花江上掌牛山河”,包括今鳇鱼岛一带,顺江而下,止于沐石河入松花江口之下的饮牛坑处(今德惠市京哈铁路桥处)。道光元年(1821年)第二次扩延,“复由饮牛坑起,至下红石砬子、石子滩止”。红石砬子、石子滩处,即今饮马河入松花江口,农安、德惠分界处。两次扩延占据了顺江而下西岸绵延近百里的郭尔罗斯前旗土地。
今鳇鱼岛,历史上在松花江西岸,即“巴彦河地方”。所谓巴彦河,并不是松花江支流,而是松花江出边之后、过了望波山向西荡出的一条大江岔。这条江岔蜿蜒北行十余公里,又归入松花江,时称“巴彦河”或“巴延河”。由巴彦河围出的狭长滩地,即今天的鳇鱼岛,时称“巴彦通”。嘉庆初年,郭尔罗斯前旗放荒、设长春厅之后,这里暂无村落,地图标注为“巴彦河闲荒”,此状况一直持续到同治、光绪年间。由于水流无常,“巴彦通”上或由小河分割,或由巴彦河改道,使其最终形成了今天由5个大小岛子毗连的鳇鱼岛。当时这里“淀多水稳”,是捕捉鳇鱼、鳟鱼的好地方,打牲衙门便将其占用了。
这段占地打牲的史实,后来被记录在光绪年间解决蒙乌两署沿江地界问题、由打牲衙门所立的“贡江碑”上:“溯查本衙门设网捕鱼:每岁冬间,本总管奏明出边,督率官弁、兵丁等,采捕鲟鳇鳟鱼并五色杂鱼,挂冰运署,报明将军会衔,分二次呈进恭祭坛庙之要贡,委非内庭口味可比。嗣因边里人烟稠密,水浅鱼稀,前于乾隆二十六年,经本省将军奏明,由边外起,南至松花江上掌,北至下红石砬子、石子滩等处止,其间沿江均为捕贡、晾网之区。”
叁 捕鳇往事
在康乾一百多年间,打牲衙门捕打鳇鱼的方式一直是秋冬连捕,每年秋后出边在江上荡捕,冬月在江上凿冰网捕,主要捕打鳇鱼,兼及其他“各色肥鱼”。但是,鳇鱼生长期长、成熟期晚,而且秋冬时节江水下落,想要在这段时间在柳条边内外松花江段捕到成年鳇鱼越来越困难。于是,为了保证捕到足够尺寸的鳇鱼,又增加了夏捕,在嘉庆初年形成定例。夏捕专门捕打鳇鱼。由此,秋冬捕时间缩短,成为冬捕。
不论是秋冬连捕,还是夏冬分捕,捕到的鱼都要在入冬后分两次向北京“挂冰呈进”,分别称“头贡”“二贡”,因此蓄养捕到的鳇鱼等大鱼的鱼圈就必不可少了。
鱼圈在当时既称“圈”,又称“泡”,还有称“渚”的,由于主要是为了蓄养鳇鱼,便统称为“鳇鱼圈”。
鳇鱼圈多选用江边的水泡子或在江岔子里围栅而成,水面大小不一,水深最少也要在三四米之间,以保证入冬结冰后鳇鱼还能在水下生存。鱼圈还要有出水口和进水口,以保证水的流动,而且在伏天里水温不致太高,防止鳇鱼受熏蒸而死。鳇鱼圈并非打牲衙门专有,凡捕打鳇鱼必备鱼圈。因为鳇鱼太大,夏天捕到后如长途运输极易腐坏,只能先就近放入圈中喂养,等待冬天。鳇鱼圈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哪处合适就设在哪儿,几年不用便淤废了。
自从打牲衙门有了“鳇鱼贡”后,鱼圈便在边内设置,蓄养捕到的鳇鱼等,今舒兰市黄鱼圈遗址便位于当时的边内。乾隆年间,打牲衙门将其打牲用地延展到边外后,便在巴彦河西设鱼圈一处。道光年间,为完成每年20尾的“鳇鱼贡”,打牲衙门不得不到更远的“讷江江面”(今松原市松花江段)荡网,鱼圈也随之增设。至清末,边外打牲用地内的“鳇鱼圈”固定至4处。宣统三年(1911年)吉林全省旗务处的公文中记载了这4处鳇鱼圈的名称:巴延泡、平安泡、吉祥泡、如意泡。
这4处鳇鱼圈是顺江排列的,都在今德惠市沿江范围,其中2处就在今鳇鱼岛所在的松花江西岔、原巴彦河(今已改称松花江)上。
“巴延泡”,《打牲乌拉乡土志》中又称“巴延渚”,设立最早,因巴彦(延)河得名。光绪二年(1876年)绘制的《长春厅舆地全图》和宣统二年(1910年)绘制的《德惠县全图》上都有标注,分别称其为“鱼圈”和“上黄鱼圈”。两图所标的鳇鱼圈位置,与“贡江碑”记载的“由望波山迤下老江身分出一岔,名曰巴延河,河西原设鱼圈一处”完全一致。
“平安泡”,《打牲乌拉乡土志》中又称“长安渚”,应在今鳇鱼岛两侧江岔汇合处、今德惠市岔路口镇马家店村北老营处自然岛的西江上,也在原巴彦河上,当设于同治八年(1869年)前。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吉林全省旗务处委员毓升等人为查勘蒙界,曾到过这里,记下了这处鳇鱼圈,称今北老营“亦在大江之右,向经乌署命名‘老营通’,租与张仁之地。周围柳通间有熟地,现被水淹。偏北有圈鳇鱼泡一处”。
另外2处,“吉祥泡”属于今德惠市松花江镇;“如意泡”(又称“如意渚”)属于今德惠市菜园子镇。这两个镇至今仍有“黄鱼圈”的地名。
每当夏捕开始,特别是有鳇鱼入圈后,这4处鳇鱼圈便开始派人看守,“每泡派打牲丁四名,轮为两班看守……其头班着以四月初一日起至八月初一日止,二班以八月初一日起至十一月内停止”。
今农安县北靠松花江边,也有黄鱼圈村、黄鱼圈乡,应来源于江边的鳇鱼圈。但从吉林省档案馆收藏的《打牲乌拉旗务承办处捕贡江界全图》上看,此处已不属于打牲衙门贡江范围。从这处鳇鱼圈的传说和档案资料来看,也不属于打牲衙门。
沿松花江往西、往北直至黑龙江,还有一些鳇鱼圈,就更不属于打牲衙门了。从当时的档案看,打牲衙门出边捕鳇,最远未过三江口,多在“讷江江面”,捕到的鳇鱼拖回打牲用地内,养在就近的鱼圈中。松花江上其他的鳇鱼圈,包括今农安鳇鱼圈,都应属于同样有捕鳇任务、沿江驻扎的副都统和协领等衙门。而黑龙江上的捕鳇任务,则由黑龙江将军负责。他们大多不设专门的捕贡兵丁,而是雇用民人捕打,也会设圈蓄养,冬月进贡。
今天的鳇鱼岛,在历史上不仅有鳇鱼圈,还有2处鱼营,其中1处还是总营。
鱼营是以鳇鱼圈为中心,供捕鱼、养鱼及打牲丁休息、过夜和值班的地方,在当时的文书里常被称为“官房”。鱼营最初是季节性的,增加夏捕后,几近常年使用。从档案及文献资料看,最初只有“贡江碑”记载的“鱼圈一处、鱼营二所”,增加夏捕后,鱼圈增至4处,鱼营也应增至4所,总营设在今鳇鱼岛上的张家大院村,当时的文书中称之为“下江巴彦河鱼营”。张家大院村原名叫“黄鱼窝棚”,东西两面都有渡口连接旱路,从东江上岸后便可进入吉林北路驿道,不论是水路还是旱路,往来都较为方便。
在以捕鳇为主、每年2次的出边捕鱼中,打牲衙门的翼领(辅佐总管之官)都要带队,有的年份总管还要亲自出边,总营便是他们坐镇指挥之所。
肆 鳇鱼之贡
每当进入冬月,总营之地便格外忙碌,各鱼圈的出圈鳇鱼和冬捕所获的“各色肥鱼”,都要运到这里过数、称重、挂冰,然后分两次装车运往京城,完成“头贡”和“二贡”。《打牲乌拉乡土志》记载:“巴延渚……界内前建有捕鱼总营一所,派官值年看守,历年冬至以前,务将进贡鲟鳇及各色鱼尾俱运此营,挂冰妥协,总管由此发贡。”《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中记载,每到此季,“各色鱼尾由驲运送巴延,总管挂冰报明,吉林将军勘验”。
每次呈送北京的贡鱼中,最大的两尾鳇鱼,皇上要亲自过目,称为“御览鲟鳇鱼”,打牲总管必须在场。“御览鲟鳇鱼”由总管选定,挂好冰后要先送到吉林城,请吉林将军会衔验看,然后裹上芦席专车呈送。清代档案中有一份打牲总管台春在今鳇鱼岛总营恭送头贡“御览鲟鳇鱼”后给吉林将军衙门的报告,展示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的贡鱼情况:“本总管现将头次应进各色鱼尾捕齐,头次应进御览鲟鳇鱼二尾,于十一月十七日由营起运……续将二次鱼尾捕足,拟于十一月十九日由营起运。总管带领二次差员花翎骁骑校连喜,将二次应进御览鲟鳇鱼二尾,亲押运省,呈请将军勘验,会衔呈进……头次共重一万二千七百十斤,二次共重一万二千五百十斤。”
伍 地权纷争
乾隆年间,打牲衙门将打牲用地扩延到柳条边外时,松花江两岸的土地还没有出放,沿江更无民屯,所以打牲衙门就在江两岸(主要是西岸)圈出大片土地,设鱼圈、鱼营和晒网场,留养江套及岸边的树木,以便取用,毫无阻碍。当郭尔罗斯前旗的土地出放后,江西岸的土地便与长春厅东夹荒、农安乡之地相连,这些地方的流民“窥伺通场为沃土,觊觎条甸如利薮”,常有侵占混淆的情况,而蒙古王公因出放荒地尝到甜头,便有将沿江土地收回“招佃输租”之请。光绪十一年(1885年),蒙乌之间在今鳇鱼岛所在的巴彦河一带首次发生争议,即“郭尔罗斯公报请本省将军,请将巴彦河附近通场撤回,招佃输租”。
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吉林将军派员会同郭前旗和打牲衙门双方人员勘察后,郭前旗要回了今鳇鱼岛南部、朝阳乡学安村所在两个岛上的大部分土地,只有于家套子部分归江东驿站“登伊勒哲库站经理,与北公输租”。巴彦河西岸南段、今朝阳乡政府所在地朝阳村以东之地,“拨给乌拉,永为捕贡之区”。边界划定后,打牲衙门在鳇鱼圈以东两署土地分界处立碑,镌明了这次分界的前因后果,这便是前文提到的“贡江碑”。
分界后,蒙古王公便将岛上和岸上的一些土地出放,今鳇鱼岛归入邻近的长春厅东夹荒二甲。长春厅升府、分设农安县几年后,东夹荒并入长春府怀惠乡,东夹荒二甲改为怀惠乡外九甲。
光绪末年,东北开发大潮兴起,长春府东面沿松花江一带垦民日增,不仅蒙古王公出租土地,打牲衙门也将自己占用的土地出租,更有机构设在江东、与江岛及西岸毫无关系的驿站、鸟枪营也过来占地出租,导致地权混乱。为此,蒙古王公再提异议,时任吉林巡抚陈昭常派长春知府孟宪彝等“与蒙员会同调查该处荒地情形,以便奏请开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孟宪彝会同“蒙员”查勘了包括今鳇鱼岛在内的沿江荒地。孟宪彝以松花江主江在东为据,认为包括“鳇鱼岛在内的沿江有争议的地方,“地亩既均在大江之西,以公理论之,更宜归之蒙公”。打牲衙门则强调,包括今鳇鱼岛北部岔路口镇马家店村在内的江上的一些滩岛,“皆系江身东滚西移”所造,属打牲丁“留养条枝”作樟杆、柴薪之用地,“实与鱼务大有攸关”,应属打牲衙门。
宣统元年(1909年)秋,吉林省派员会同各方勘查无误并磋商后,将沿江岛地一次划分清楚:今鳇鱼岛北三岛,即当时北老营、江心馆所在的岛(今属岔路口镇马家店村),由蒙古王公与打牲衙门折半剖分;对不属于今鳇鱼岛的“如意通”地方(今属菜园子镇)也予以划分。当时在江心馆有农民张仁租种土地,在于家套子有于姓农民租种土地,这是至今在文献上能查到的鳇鱼岛上最早的开垦者。
此后,今鳇鱼岛及江边归属蒙古王公的土地被归入长春府怀惠乡外九甲,德惠县设立后由其管理。
民国时期,德惠县沿江蒙地地权继续保留,打牲衙门、驿站和旗营所占土地一律收归国有。1919年,吉林省荒务总局对这片土地予以丈放,总面积2932.62垧。
(作者孙彦平为吉林省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来源: 长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