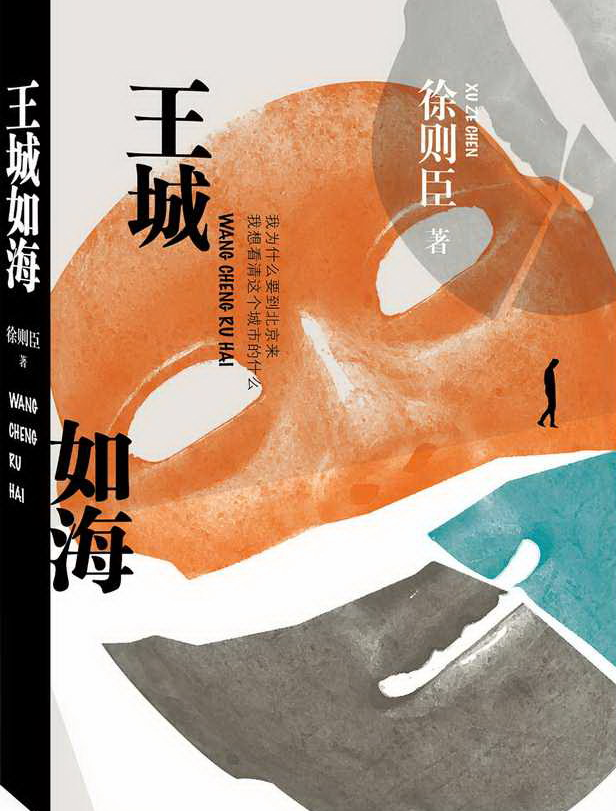
《王城如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开门撞见的就是现实问题
记者:小说的主角、海归戏剧导演余松坡说自己是一个“无条件的现实主义者”,怎么理解这个说法?
徐则臣:很奇怪,余松坡在国外云游的时候可以做一个纯粹的先锋作家,但回到中国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或者他必须尝试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处理遇到的问题。在国外,经常有外国作家问,中国作家为什么都那么沉重,为什么大部分都采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我说,国家大,人口多,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导致我们有极其复杂的现实,这些复杂的现实完全包围、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你一开门撞见的就是各种现实问题。扑面而来的问题解决不了,你很难从现实中跳脱出来。在国外,一个平稳的、饱和的、一潭死水一样的中产阶级社会,绝大多数问题都不会影响和改变你的生活,社会的变化你可能都感觉不到切肤之痛。作家可以很容易跳脱出来,自由放松地去处理精神的问题、艺术的问题,你尽可以与现实无涉的空间玩得转。所以,当余松坡发现不能从众多的现实问题脱身而出时,他就要去考虑如何艺术地处理他认识到的一些现实问题。他是一个先锋戏剧导演,他希望把先锋艺术的一些方式带进来,用以处理中国的现实问题。
记者:《城市启示录》里引起争议的对“蚁族”观点,你自己赞同吗?
徐则臣:说真话,我没有一个鲜明的立场。小说里也有不同的人物在争论。一个年轻人说,我没有失败,只是现在没有成功而已。年轻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一个人的路也可以是所有人的路。不能从一个功成名就的立场和高度去指责年轻人,这肯定是不合适的。
不过事实上,蚁族的确存在很多问题。我赞成年轻的时候追逐自己的理想,无论条件如何恶劣、艰苦。单个人没有问题,但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干,那就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了。不是否认理想主义。《城市启示录》里的教授非常沉痛地说了那么一句:“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他的沉痛让年轻人很不舒服。年轻人处在现在的境况里,更多地应该是被鼓励,被扶持,而不需要一个老先生对我们居高临下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态度有伤年轻人的尊严。
我们讲故事的传统太过强大
记者:我记得你说写《耶路撒冷》的时候案头总放着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写《王城如海》的时候常翻看什么案头书?
徐则臣:喜欢的书我都会翻。很多作家写作时,喜欢找跟自己的调子比较接近的书看。我找的未必非要跟我接近,但必须是能激发我、有助于形成自己的调子,或者刺激我的叙述欲望的作品。
写《王城如海》跟写《耶路撒冷》时不一样。写《耶路撒冷》的时候,看的都是大长篇,四五十万字,或者更多,因为它相对舒缓,语言的密度更大。写《王城如海》的时候看的都是在十来万字的小长篇。我要找节奏。比如奈保尔的几个小长篇,比如奥兹的《我的米海尔》。有的时候也会逼着自己沉下来,因为叙述的节制容易让你在写作时节奏越走越快。所以写一段时间,我就得把自己往底下摁一摁。那时候就要看一些大部头,比如手头的君特·格拉斯的书,比如乔纳森·弗兰岑的书。
记者:50、60后的作家挺愿意尝试先锋的小说写法,现在的70、80后的作家似乎很热切地拥抱现实主义。这种趋势的原因是什么?
徐则臣:老作家也处理现实问题,但手法上考虑会更多一些。年轻作家在处理现实题材时,反倒经常疏于考虑别致的手法。有可能是他还没到创新的地步,他得先把一个故事写成功了。他要写得耸人听闻,震撼人心;这样更容易引起关注。写作的时候可能既没有宏观的文学史概念,也没有自身的、一个人的文学史概念。但是一个成熟作家,比如50后的作家,他有足够的经验和背景知识,他会考虑,这部作品在他整个写作生涯里是什么定位,包括题材的定位,写作方法、技巧、结构的定位,他的这部作品和其他作品之间的差异性是什么。年轻人有时候慢不下来,抓住一个题材就扑上去,写完再说。
记者:你考虑过《王城如海》在个人文学脉络和宏观文学史上的定位吗?
徐则臣:《王城如海》和《耶路撒冷》完全不一样,它和当下很多小说也不一样。区别在于,《王城如海》有一种强劲的思辨性,它靠一些思想性的东西去推进,我们大多数小说是靠故事情节推动。
很多智性写作的作家都是靠思辨来推进小说,比如学院派的索尔·贝娄。有一次,一个批评家问我喜不喜欢索尔·贝娄,他在《耶路撒冷》中看到了一些索尔·贝娄的气息。我告诉他,我非常喜欢索尔·贝娄,写《耶路撒冷》的时候,我看了很多索尔·贝娄的书。索尔·贝娄这样的作家在中国极少,尤其在年青一代作家里。年长一代里也不多,中国作家主要靠讲故事。我们盛产故事。海量的中国故事成就了中国作家,可能也坑了中国作家。
我们讲故事的传统太过强大,以至于让年轻作家认为这是唯一的正道,是写作的正途。好像离了传奇性的故事的讲述,一个小说家就会变得非常可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