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文学评奖何以一次比一次难尽人意?评委们为什么难以与作家在小说艺术的内在审美价值上进行同一高度的对话?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与茅盾先生设立此奖的原始动机是否存在距离?评奖的价值取向,即对现实主义原则的维护和对史诗品格的强调,如何制约了审美品性更为丰富、多元的优秀之作涌现?……”
这些锐气逼人的追问出自洪治纲,曾给文学界带来深深的震撼。那是在1999年,这篇题为《无边的质疑》的文章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之后,获该刊当年度优秀评论奖。第二年,洪治纲又获颁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
作家艾伟曾评价洪治纲:“就像皇帝新衣里的那个孩子,他的声音可能是刺耳的,当然也可能是孤单的。”如今,18年过去,“那个孩子”已过知天命之年,他对文学批评的初心是否不曾改变?无论如何,洪治纲是当代非常重要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其文章和著作受到广泛重视。

洪治纲
当代的文学批评为何不能让人满意?很多重要评奖为何屡遭质疑?评论家和作家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意义何在?……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洪治纲教授。因为他的《余华评传》修订版(作家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刚刚出版,谈话就从他对余华的研究开始。
谈余华:他正在为他的新小说“做人工呼吸”
中华读书报:开始写《余华评传》是在你读博士期间,为什么选择余华?
洪治纲:2003年,我正在浙江大学攻读在职博士期间,突然接到一家出版社的写作任务,希望我写一本《余华评传》,我便着手对余华的生平和创作资料进行搜集与整理。我之所以接受这个任务,是觉得自己有几个较为明显的优势:一是我对余华的作品相对熟悉,对他的研究材料也一直在进行跟踪式的搜集;二是余华的人生经历相对单纯,而且与我差不了几岁,基本上可算是同一代人,精神沟通的效果会比较理想;三是在余华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中,有三十几年都是在浙江度过的,采访起来也方便。但事实证明,我有些想当然了,在写作过程中,很多重要史料的求证,依然要花费巨大的力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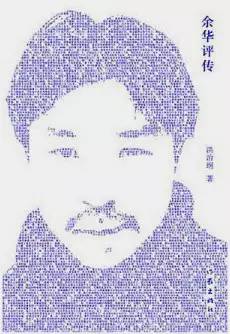
《余华评传》,洪治纲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39.00元
中华读书报:见余华是什么时间?对他什么印象?
洪治纲:我第一次见到余华的具体时间已经忘了,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那时候我已经发表多篇有关余华小说的评论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挺牛气的,那时候的先锋作家都差不多,比较狷狂。
中华读书报:在写评论的过程中,和余华有过怎样的交流和探讨?你的评价会找他印证吗?
洪治纲:我和余华做过很多次对话,对余华的创作以及生平都进行过求证。在具体的评论过程中,针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我们也会进行深度交流。譬如,他的早期小说中会随意处理人物的死亡,几乎每篇小说中都有几个人物要非正常地死掉;再譬如他非常喜欢在小说中使用精确的数字,从某年某月某日到某本书的第几页,再到吃了几碗面,这些精确数字的叙述有何动机;譬如他对先锋文学的理解,等等。当然,更多的还是闲聊阅读和生活。
但在我的具体评论中,从来没有找过他来求证某些观点。这是因为评论家的阐释有他自己的思考和自由空间,同时余华也从来不相信评论文章对他的创作有多大影响。当然,偶尔看到有意思的评论,他也会和我交流。
中华读书报:你和余华私交如何?这种交情对于做评论有何影响?
洪治纲:我一直觉得,我与余华之间的交往,基本上是君子之交,对我从事余华作品的评论基本上不产生影响。每年都会有一两次碰面的机会。在碰面时,只要时间允许,我们都会细聊一些他的创作情况。有时因为资料难以搜集,我也会找余华索要,一般他都会及时寄给我。我评论余华创作的所有文字,从来不预先拿给余华看。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因为长期跟踪研究余华的创作,我对他的作品,肯定性的分析更多一些。
中华读书报:有着持续跟踪阅读和评论,你对余华创作的轨迹可否做些概括?从此前的一致叫好,至《兄弟》《第七天》之后的作品引起的“两极化”争议,你怎么看?
洪治纲:我在修订《余华评传》时,对余华的作品进行了一次重读,并完成了一篇《余华论》,发表在近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1990年之前,余华是以背对现实的先锋创作闯荡文坛,其小说呈现出明确的主观真实之特点。1990~2003年,余华开始以批判者的眼光关注现实和历史,着力探讨人物的命运与历史之间的内在关系。2004年到现在,余华更多地关注当下的现实生活,并以明确的解构手段,揭示现实的混乱和喧嚣。从他的创作与现实的关系来看,余华的创作轨迹可以描述为“逃离现实——批判现实——解构现实”这样一条主线,当然其中包括了余华较为复杂的主体思考和心路历程。
对余华作品的“两极化”评价,特别是国内对《兄弟》和《第七天》的“两极化”评价,有着非常复杂的文化背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众多读者对余华小说的阅读已形成了某种审美定势,特别是由《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代表性作品所产生的悲剧性审美定势,固化了读者对余华创作的审美接受。所以,当《兄弟》和《第七天》等解构性的叙事出现在读者面前时,读者的审美定势被颠覆了,无法很好地接受它。此外,中国作家对当下现实的直接表达,因为有着丰富的现实经验作为参照,导致人们在阅读中常常纠结于生活的真实,而游离了艺术的真实。但国外的读者,因为不是特别熟悉中国当下的现实生活,反而能够在一定的距离感中来接受这两部小说,因此,《兄弟》在国外几乎是一片叫好。
中华读书报:你认为余华最好的和最失败的作品分别是什么?你如何评价他在中国作家中的地位?
洪治纲: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品是《在细雨中呼喊》和《许三观卖血记》,最不喜欢的是《四月三日事件》——但这未必是他最失败的作品。
就我个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而言,我觉得他依然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几位作家之一。如果大家有机会读一下他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或许能够发现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切思考,以及他内心深处的情怀。
中华读书报:你认为余华目前的创作处于怎样的状况?他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洪治纲:我的直觉是,余华的创作目前还是处于某种胶着状态。他自己也说,现在手头有三部小说都写了一些,但都无法完成,“正在做人工呼吸”,哪一部能够首先苏醒,他自己也不清楚。其实这种胶着状态,是每一位成名作家都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都渴望自我的超越,渴望更大的成功。如果要说余华目前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如何获得较为完整的思考和写作的时间。我们在一起聊天时,聊到最多的就是他缺少完整的时间,社会交流(包括国际交流)占去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中华读书报:《余华评传》于你的创作和评论而言,有怎样的意义?
洪治纲:对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精细的研读,可以为你找到一个深挖下去的“点”,而有了这个“点”,你再回到某些“面”上,就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值得研究。我在完成《余华评传》初版时,就觉得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具有鲜明的代际共性,于是,围绕这一代作家,我在2009年出版了《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一书。而当我做完了“60后”作家群的研究之后,一个有关中国当代作家的代际差别问题也随即涌现出来,由是,我又转入到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之中,直到2013年才完成《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一书。因此,从自己的专业发展来看,《余华评传》对我确实有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