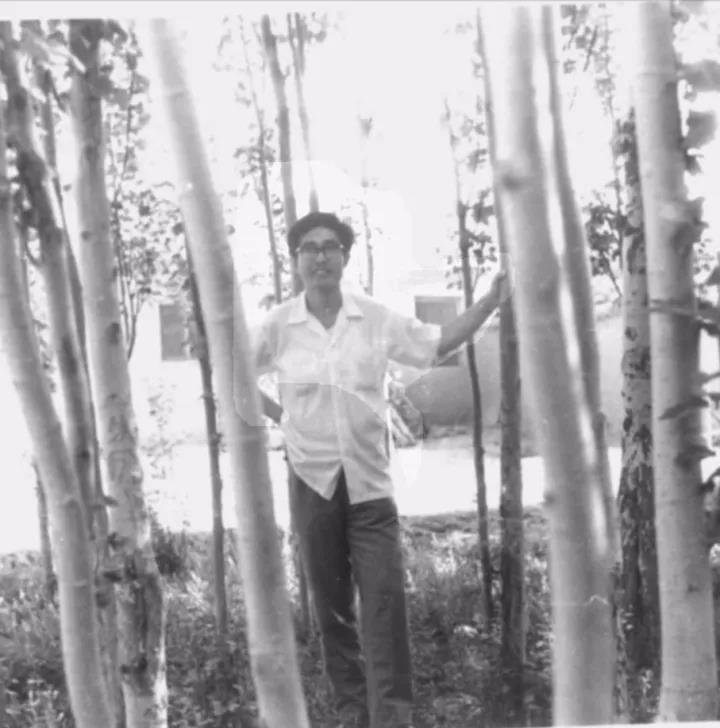
年轻时的陆天明
我们都是幸存者。我们怎么活过来的?应该怎么活?怎样才能把国家和民族变得更好?
记者:小说取名《幸存者》出于怎样的考虑?
陆天明:写这部作品我一直抱着写成一点算一点的想法,毕竟年龄摆在那儿。“幸存者”有多种解释,也有朋友质疑、担心。但后来我坚定用“幸存者”为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人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面前,站在黄花岗72烈士墓园前,站在所有为强国梦而献身的那些先驱先烈们面前,我们都是幸存者。我们怎么活过来的?应该怎么活?怎样才能把国家和民族变得更好?从这个角度切入,去呈现一代“幸存者”的命运和经历,无可非议。理所当然。在探讨这个重大主题时,我觉得要赶紧说、赶紧写,毕竟我们有过一段前无古人,我想后也不可能有来者的经历。
记者:在您的第一部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中,也有一个叫谢平的主人公,您说这是之前唯一一部有您影子的作品。后面几部长篇,尤其是《苍天在上》等影响非常大的几部反腐作品,里面并没有多少您的影子。两种类型的创作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陆天明:非常不一样。我前面几部作品,尤其是反腐四部曲,社会影响还比较大,我在创作中也很真诚,但更多考虑的是社会认同,更清醒地知道我是在摹写社会,表现时代、他人。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我在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些年来,一些作家朋友不认可现在“为社会服务”“为人民大众写作”的创作理念,觉得只要服务自己、表现自我就行了。但这是我重要的文学理念之一。文学要为社会服务,要介入社会。但《桑那高地的太阳》和《幸存者》等作品,我很明白是写我自己和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幸存者》。我这次给自己的写作要求是: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遵照一个标准,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人民大众。我要把我们这一代人表现好。为什么?因为这一代人是“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当然这个“最后一代”的概念有争论。理想主义者还会有,但不同时代的理想主义者的追求会不一样。我们这一代是空前的以追求无私为自己生存目标的一代人,这个过程中经历坎坷,做了奉献、牺牲,也有反省,给历史留下了一段很值得思考的宝贵的东西,我感觉这些就像焰火一样闪了一下夺目璀璨的光,迅速消逝了。这其中有多少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有多少哲学的东西?有多少东西是必须摒弃的?值得后人考虑。几许艰辛踯躅,只能概括在“幸存者”这三个字里。前些年我在为自己一个文集写的序言里写过这么一句话:“剖开这些文字,应会有血流出来”,这依然是我对《幸存者》的期许。
记者:《幸存者》中也涉及到腐败问题,这似乎是您的作品一直关注的主题?
陆天明:我是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到北京的,我为什么要开始写反腐小说?了解我的人都说,天明,你其实没有变。我们这批城市里重点高中的学生,放弃高考,注销上海户口,从大上海去到新疆,走工农结合的道路,当年这么做,真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只想到工农中间去,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但到了农村和农场,看到一些蜕化变质,发现了毛泽东所担心的,包括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担心的一些干部的变化,脱离群众,腐败滋生,完全忘记初衷。我们看了后深有痛感。我调回到北京,写反腐,还是这个初衷。我的第一部反腐作品《苍天在上》,就是想呼唤苍天,中国你不能腐败。写这部戏,最初没有情节,没有人物,什么都没有,但题目有了,就是《苍天在上》。当时就想喊这么一声。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春天来了,科学的春天来了,人民的春天来了,但腐败也来了。老百姓想不通,我们也想不通。这种情感一脉相承,也就是现在说的不忘初心,要把中国搞好,中国共产党不能丢掉初心。
我们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比你想象的要多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任何时代都有一批理想主义者,但都是人群中的少数?
陆天明:我们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比你想象的要多。1963年、1964年,上海第一批到新疆去的支边青年,报名三万,批准一万。许多青年都写了血书,坚定扎根边疆。有的家长把女孩关在楼上,不让出去。我们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谈恋爱那样,从楼上把被单系好,溜下来到街道报名去新疆。这不是个别的,很多都是这样热血沸腾过去的。这一批人,是典型的,但不能说代表全部。我通过这部小说,很想告诉大家,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一群年轻人,也想让大家知道年轻人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我认为,中华民族要复兴,要实现中国梦,不可能让所有年轻人都走这条路,但这里面的精神因子还是需要的。被认为有很多问题的“80后”,现在已经是各个岗位上的重要人物,什么道理?当历史和社会把担子压到每一代人身上后,他们一定会成长,会承担起民族和国家的使命,因为历史是往前走的。对年轻一代,我们永远抱有希望。
记者:小说中谢平和父亲的关系很打动读者。谢平和父亲关系的紧张,是否也是他去新疆的重要原因?在后面两部的写作中,谢平和下一代的关系,是否会是您考虑的一个重点?
陆天明:写父子关系是从塑造人物出发。每个人物有特定的生存环境。谢平去新疆主要是理想信仰,当然也和家庭有关系,想给家里减轻负担。我也是家里的老大,从小没有父亲,只有母亲,我去新疆是为了革命,也想为家庭减轻负担。至于说到父子关系,在文学创作中是永恒的主题,尤其是父子关系往往最能够凸显时代的意义。父子矛盾冲突,不仅是生理上、心理上的,而且是时代的、文化的。这种矛盾,在两代人之间永远会存在,如果不存在,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就停滞了。三部曲后面还会写到谢平和他的儿子之间的矛盾,他变成父亲后如何对待父子关系?如何看待父子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悬案,要重点写。通过父子关系写时代变迁,有文学意义,也有社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