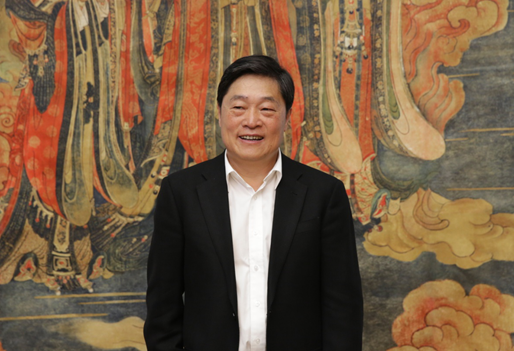
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是我讴歌的对象 不平凡的人既仰望星空也会俯瞰大地
在《张居正》获得成功之后,熊召政又利用十二年,创作了一部《大金王朝》。熊召政说,他长期喜欢写诗,又喜欢阅读历史,把历史和诗结合起来就是史诗,“我愿意选取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推动过历史前进的人物,作为我写作和讴歌的对象,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熊召政,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湖北省文联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故宫博物院、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已出版长篇历史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历史札记、诗集四十余部。其中,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摘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1979-1980年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话剧《司马迁》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在首都剧场连演52场,场场观众爆满,被专家誉为近年来最优秀的历史话剧。目前,历时十二年精心创作的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大金王朝》第一卷《北方的王者》及第二卷《擒龙的骑士》已完成,第三卷《帝国的坍塌》将于今年完成。
对谈嘉宾 熊召政
特邀对谈人 谢新
1 我长期喜欢写诗,又喜欢阅读历史,把历史和诗结合起来就是史诗。好的历史小说就应该是完美的史诗。
谢新:熊老师,你好!你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大金王朝》,以及北京人艺的话剧《司马迁》(编剧),讲述的都是中国历史人物。而你的文学创作起步却是源于诗歌。在你的个人简介中,你也总喜欢把诗人放在第一位,诗歌可以抒发情愁壮志,千般风情,一腔豪迈,而历史题材作品则需要追根溯源,引经据典,不失史实。今天,想请你谈一谈你的文学创作经历。
熊召政:《张居正》获茅盾文学奖之后,我在香港参加国际书展,香港一位记者问我,你是一位诗人,你要转行创作历史小说,这里面有什么诀窍吗?我说,诗和历史,是我从小就喜欢的两样门类。我的文学之路从诗开始,二十六岁时,我写的第一首长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全国中青年优秀新诗奖。因为诗最早出名,别人把我当作一位诗人。我长期喜欢写诗,又喜欢阅读历史,把历史和诗结合起来,就是史诗。好的历史小说,我个人认为,就应该是完美的史诗。不过,创作完美的史诗一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越艰巨,这部史诗也会越绚烂。
谢新:所以,你的众多作品,离不开一个“美”字,这样的文章读起来也耐人寻味。徐迟和姚雪垠两位大家对你的文学创作起到了引领作用。姚雪垠曾说过,他需要一部能够死后垫后脑勺的作品,即能让自己满意,同时也让读者满意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可以说是完成了他的夙愿。你花了十年时间创作了四卷长篇小说《张居正》,按理说《张居正》也算是你对作家这个职业最好的佐证了。可是,你又选择另一个十年用于创作了囊括辽、金、宋三国的历史小说《大金王朝》,你为什么要作一个这样的选择?通过这部作品,你想带给读者什么?
熊召政:《张居正》获奖的时候,我有一个获奖感言,讲得很简短。我说,我愿意选取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推动过历史前进的人物,作为我写作和讴歌的对象。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我写《张居正》,是因为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家。后来因为某种机缘,我到了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当年金朝的那些人物从这地方走向了中华的大历史。应当地政府的邀请,我走访了大金王朝的很多历史发生地,以及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乡。我深深地为他们从故土走出边陲、走向中华历史的事迹所感动,这些事迹也引起我的思考。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我心里有了整部作品的脉络。中国的二十四史中,有一部是《金史》。我在深入研究的时候,发现辽金宋三国,是中国中世纪的大三国,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三国。这里面有契丹人、女真人、汉人,当然也包括西夏的党项人。而东汉之后的魏、蜀、吴只是小三国。我觉得辽金宋大三国比起魏蜀吴小三国的历史意义更大,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各个民族创造的文化。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来书写多年前的这段历史,对今天有特别的意义。我在写的过程中,对于女真人的大金国灭辽灭宋这一历史事实,通过史料的研究,也确立了我的历史观,主要有这样三个论点:第一,不是一个边缘的、粗俗的、野蛮的少数民族,战胜了文化优越的汉民族,而是草根的、新兴的、健康的政治集团战胜了腐朽的、没落的贵族集团。第二,中华民族的传承,有时候是靠文化的继承、弘扬和发展,有时候是靠民族之间的融合甚至是争夺来完成。第三,为什么强大的宋朝会败于一个弱小的民族?就是因为大宋王朝在宋徽宗的领导下,迅速变成一个娱乐化的国家,娱乐至死是一个人类性话题,也是一代一代的读书人挥之不去的忧患。我想,通过自己的书写和思考,来解释这样一个历史的规律。
谢新:《张居正》和《大金王朝》同属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你在创作上的着力点有何不同?
熊召政:我可以借用苏轼的《行香子》与《水调歌头》来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是“都将万千,付与千钟,任酒花白,眼花乱,烛花红”的万历首辅搅动的朝政风云;一个是“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的各路豪杰沙场征战。《张居正》这部历史小说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而《大金王朝》是金戈铁马下的政权更迭,一样的惊心动魄,不一样的人物命运。我写历史小说《张居正》的背景是邓小平南巡,当时我在深圳,看了《晚间新闻》播放的新闻,《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东方吹来满眼春》。我突然意识到中国的改革要出现第二个高峰阶段了。当时有朋友问我,“你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改革成功的案例?”我想改革的意义对历朝历代都极为重要,研究改革也是一个学者的使命。此后,我开始寻找历史上的改革案例,着重研究了张居正。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改革最大的问题,到最后还是人的问题。如果用清流主持改革,他们认为不可更改的“清规戒律”太多太多,他们不敢承担道德的责任。而真正的改革家需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不下地狱”的精神,需要有干大事、成大事的心态和气魄。经反复研究,走访张居正故居遗址,查访近千万字的史料,我发现张居正在改革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张居正提出“重用循吏,慎用清流”。清流之辈往往只说不干,碰到体制上的问题绕着走。循吏就是怎么能干成事就怎么干,他们比较有开拓精神。所以,我觉得改革的关键,就是用什么人来主导改革,让什么人来参与改革。改革没有一个总设计师是不行的,改革的团队建设非常重要。我在《张居正》这部小说里面,就确立着这样的历史观,即“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现实中我们很多人实质上是叶公好龙,说起来头头是道,碰到实际问题就抹不开了,回避问题绕开难题。这样是没有出息也毫无意义。《张居正》这部长篇小说获茅盾文学奖之后,我又萌生了写《大金王朝》的想法。
我在《大金王朝》序言里面,阐述了我的观点,前面也提到过,宋徽宗登基以后,忧患意识严重缺失,娱乐至死终结了这个朝代。北宋的江山子民在他十九年统治时间之内,迅速走向娱乐化,向南方逃窜的势豪大户,王公贵族南渡杭州之后,依然不改娱乐的习气。纵观这段历史,我才提出这样的观点,一个民族可怕的是丧失了产生英雄的土壤。当所有的君子、英雄谢幕,小人就会粉墨登场了。小人政治在宋徽宗时代达到了高峰,这是娱乐至死的政治基础。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政权一旦丧失了忧患,丧失了为民族思考和承担的能力,娱乐至死的风气蔓延是极危险的事情。一个民族应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的英雄气概,才有无尽的希望。这是我在创作时的一些历史思考。《大金王朝》这部长篇小说,目前已经出版了第一卷第二卷,按我的写作计划明年会全部完稿。《大金王朝》与《张居正》写作有很大的区别在于叙事更宏大,更波澜壮阔,写作时也更艰难,挑战性也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