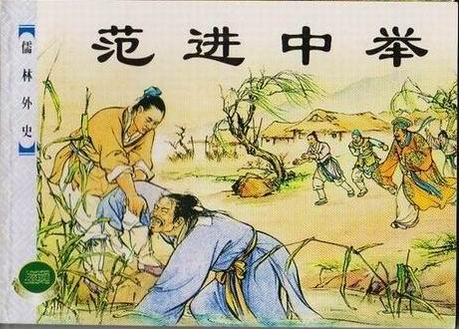
连环画《范进中举》(网络图片)
吴敬梓笔下的反面人物,如贪官坏官王惠、周守备、江都知县之流,科举场中小人范进、张静斋、严贡生、卫体善、隋岑庵之类,纨绔子弟汤大爷、汤二爷,为富不仁的盐商万雪斋、宋为富,伪名士景兰江、支剑锋,骗子手张铁臂、洪憨仙、牛浦郎,势利小市民胡屠户,流氓权勿用,马屁精成老爹等等,无一不是道德沦丧的不堪之辈。作者描写这些人,深刻地暴露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尽管那时乃是所谓康(熙)乾(隆)盛世。鲁迅先生说得好,《儒林外史》一书“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师官、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象,如在目前”(《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这样的小说,我们现在看去,似乎应当是不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而当时的评论家却深刻地指出,恰恰是这样暴露性的作品足以“振兴世教”(惺园退士《儒林外史·序》)。清朝文字狱很厉害,许多小说被清廷和地方政府查禁,而《儒林外史》从来不在其列。此中的道理,同沙皇并不否定《钦差大臣》是同一个道理。
与“伪儒”小人对立的是“真儒”君子。全书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用极大的热情塑造了一个王冕的形象,这位名士型真儒的光辉形象与历史上的王冕相去甚远,无非意在开门见山地树立一个道德文章的楷模。小说里的王冕“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而又一味高蹈,不要功名利禄。王冕对于科举制度可能会产生的弊端深感忧虑,说是“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利禄之途既开,必有人以为唯此唯大。
但是科举制度的存在自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制度能代替它。所以吴敬梓笔下的正面人物也都走过读书应试的道路,例如首席“真儒”虞育德二十四岁中秀才,四十一岁中举人,五十岁中进士,走完了科举的全程;然后出任南京国子监的博士。杜少卿是秀才,庄绍光应过征辟。问题不在制度,而在人,在人的道德修养。“文行出处”亦即士人的品德修养,乃是《儒林外史》评判人物的主要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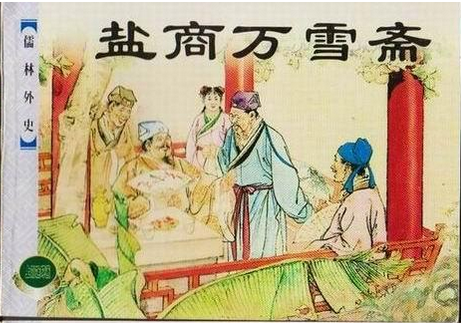
连环画《盐商万雪斋》(网络图片)
《儒林外史》中用十分郑重的笔墨描写虞育德博士为首的一批“真儒”以古礼古乐祭泰伯祠的盛典,正是要树立正面样板。小说的第三十六回“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从这位“真儒”的诞生写起,一路写到祭泰伯祠的高潮,虽然艺术上并不能算成功,却流露了作者满腔的热情。小说借一个人物之口道:“看虞博士那般举动,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已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自然不能行出来。”这正是孔夫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主持泰伯祠祭典的另一位真儒庄绍光是杜少卿“所师事的人”,此公出身于书香门第,早有文名而未尝出仕,“闭户著书,不肯妄交一人”。他也曾应过皇帝的征辟,尽过君臣之礼,很快就复回故乡“著书立说,鼓吹休明”。这个人物的模特儿据说乃是吴敬梓敬佩的理学家程廷祚(1691~1767),其人早年信仰过颜元、李塨一派的学说,后倾向于程朱理学,终身未仕。首先倡议祭祠的迟衡山满口“礼乐兵农”,颜李学派的色彩更浓厚些。吴敬梓也讲理学,又接受过颜李学派的思想影响,所以也相当重视“礼乐兵农”这些实用的知识,而放在首位的则是德行。
《儒林外史》中还有一些人物不尽同于虞育德博士等纯儒,但仍然是道德高尚的。例如被称为“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的杜少卿,他是不大看得起科举功名的,中过秀才以后就不再考了,甚至还装病不应征辟,就留在南京“看花,吃酒”,后来穷到卖文为生,仍然“心里淡然”。中国历来有这样的名士派文人,意态萧散甚至狂放,但并未违反基本道德,不过很有些儒道合一的气息而已。杜少卿最著名的一件事乃是携着他妻子的手游清凉山,吓得两边的游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这多少有些突破了传统的风习,但并不构成道德问题。他反对纳妾,笃于夫妇之情;又特别重视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其人的道德仍然是传统的、高尚的。杜少卿的表叔庄濯江,早年同别人合伙经营典当,后来合伙人穷了,他就把自己的财产拱手相让,自己独自转徙经营十几年,“又自致数万金”,这样开拓型的商人,可谓儒商,也是正人君子。吴敬梓支持当时商品经济繁荣背景之前出现的这种新人,而这些新派人物仍然是道德高尚的,值得赞许。
吴敬梓的出身和教养都决定了他不会否定科举制度。他生于累代科甲的阀阅人家,不到二十岁就中了秀才,参加过几此乡试,未能中举;到三十六岁那年(乾隆元年丙辰,1736)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鸿辞科,他参加过省考,但因病未能正式入京应试,对此他是很有些遗憾的,到临去世的前一年即乾隆十八年(1753),他在《金陵景物图诗》之末,还郑重地自署“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辞……吴敬梓撰”,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以此为荣。
吴敬梓没有也不可能否定科举制度,他只是痛恨在这个制度实行的过程中,有若干读书人忘记和违背了传统的道德,走上了邪路。惺园退士在《儒林外史》的序言中说,此书“善善恶恶,不背圣训”,“足以兴起观感,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这话虽然听上去似乎比较陈腐,其实合于原著的实际。世道人心,是每个时代作为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不关心的问题,这恰恰不是反对现行制度,而是从本质上支持政府,维护社会的稳定,希望有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