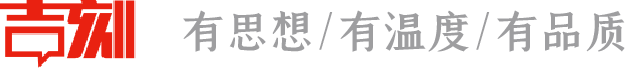在长白山西麓的莽莽林海与松花湖畔的山水之间,蛟河这片古老的土地承载着一支特殊族群的文明记忆。作为巴拉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处村落,都镌刻着巴拉人千年繁衍的足迹,流传着巴拉人的英雄莫尔根的故事。从明末清初遁入深山的渔猎部落,到如今融入现代社会却坚守文化根脉的独特族群,巴拉人用数百年的生存智慧,在东北的林海雪原中书写了一段鲜活的文明篇章。
从女真余脉到深山族群
巴拉人的历史渊源与明末清初女真各部的统一进程紧密相连。其先祖本是东海女真窝集部的分支,万历年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各部、构建满族共同体,展开了频繁的征讨。这场统一之战并非一帆风顺,在拉林河、阿什河、蚂延河流域及松花江中游一带,均遭遇了当地部族的激烈抵抗。战败后,部分女真人被俘并入八旗随军征战,另一部分为躲避战乱、拒绝征服,遁入张广才岭、老爷岭的深山密林之中,过起了与世隔绝的游猎生活。因未被编入八旗、不隶旗籍,这些深山族群被满族统治者称为“巴拉玛”(满语意为“狂野之人”“无拘无束之人”或“行为轻狂之人”),后简称为“巴拉人”。
蛟河因地处长白山腹地,山高林密、水源充沛,成为巴拉人世代栖息的核心区域。事实上,这片土地的历史脉络始终与女真先民的生存轨迹交织:从唐渤海国时期的满族先民聚居地,到金代女真人的主要活动场域,这里为巴拉文化的孕育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土壤。张广才岭作为巴拉人的核心聚居地,北起松花江、南抵东西老爷岭,山林茂密、物产富饶,盛产虎、鹿、熊、狍等野生动物及冷水鱼类,为巴拉人的渔猎生计提供了充足资源。
适配林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以渔猎为核心的生产形态。长期的山林隔绝生活,让巴拉人完整地留存了女真族古老的渔猎生产方式,渔猎既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核心生计,也塑造了族群独特的文化肌理。春季捕鱼,秋冬狩猎,松花江的细鳞鱼、鲟鳇鱼,深山的狍子、野猪、熊等皆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
巴拉人的渔猎智慧,既凝结在代代相传的工具之中,也蕴藏在朴素的生态准则里。地弩(萨斯哈)、套子(遮苏鲁)、箭(乌录)、矛枪(吉达)、夹子(改金),以及冬捕专用的捋钩和搅罗子等原始工具沿用至今;“春不打母、秋不打公、夏不打崽”的山规,彰显着他们对自然的敬畏,维系着人与自然的平衡。
不同季节,巴拉人的渔猎形式各有不同。大规模狩猎集中在冬季,由猎长(阿布达)带领全村青壮年进山,猎犬负责维护安全、协助捕猎,马爬犁承担运输重任。猎物分为食用类(野猪、熊、狍子、鹿等)和皮毛类(狐、貉、水獭、紫貂等),分配规则公平有序——个人捕获的归个人所有,集体捕获的则由阿布达平均分配,确保无猎获者也能分得一份。冬季狩猎结束后,山上会举行庄重的祭猎神(班达玛发)仪式:阿布达充当萨满,点起篝火,用小锅(汉楚)煮熟肉类祭神,伴以歌舞。仪式完毕后,众人方才带着猎物返回村落。春夏季节的渔猎则以家庭为单位,氛围更为轻松,春季捕捉大雁、水鸭子等野禽,夏季垂钓冷水鱼类,时常能捕获十几斤重的大鱼。
值得庆幸的是,巴拉人的古老捕鱼技艺得以延续,旋网、鱼钩、皮筏、扒网等原始工具仍在使用,尤其冬日湖面,捋钩与搅罗子等传统冬捕工具依旧能在冰层之上演绎出最古朴的捕鱼场景,在蛟河富江村苏尔哈屯一带,这份传统渔猎方式至今得以保留。
适配自然的居所与服饰。巴拉人的居所充分体现了适应山林环境的生存智慧,核心民居为半地穴式的“乌克墩”(俗称地窨子),多依山傍水、靠近泉水建造,向东开门以迎朝阳。乌克墩外围建有“嘎满”(护墙),防止牲畜踩踏屋顶,护墙外还有套院墙,院内设有高架仓房、猪圈、马圈,且在院门两旁及围墙周边设有多处狗窝,形成严密的居住防御体系。
服饰则随季节更迭调整,尽显实用主义。冬季穿反毛皮大衣、鹿皮乌拉(皮靴),保暖御寒;夏季着自染麻布衣物,轻便透气;草编蓑衣与蒲草鞋则是应对阴雨天气的必备装备。此外,巴拉人还擅长制作滑雪板,选用盘口粗的楸子树劈成薄板,烤弯成型后钉上鹿皮脚套,再用野猪油煨透,搭配前端装锋利矛头的榆木撑杆(兼具梭枪功能),可在雪野中快速追逐猎物,这一技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仍有老人掌握。
山林馈赠的饮食与交易。巴拉人的饮食习俗与渔猎生产紧密相关,喜食烧烤与炖菜,常用芭蒿、山花椒等野生香料调味,自酿黄米酒与豆酱,将山林馈赠转化为舌尖美味。春季食用野禽与野菜,夏季以鱼类、田鸡蛙为主,冬季则享用狩猎所得的兽肉;产妇产期需吃鱼肉、田鸡蛙及拉拉粥,认为可保证奶量充足。
由于地处深山,巴拉人的商品交易较为原始,早期以村落内或村落间的物易物为主,例如用一张猞猁皮换一毛落(类似升的量器)黄米,用一张熟鹿皮换两张生鹿皮,交易中无斤斤计较之风,双方多能各得其所。清代中期后,出现了集体商队交易模式:由一两个村落组成商队,选出“垛勒达”(买卖长),在冬季大雪封山时乘坐马爬犁或狗爬犁,携带皮货、鹿茸、人参、野兽肉等山货,前往阿城(阿楚哈)、拉林、烧锅河子等地,换回酒、黄米、粉条、盐、皮硝、铁器等生活必需品。
镌刻在地名与民俗中的精神印记
“写在大地上的历史”:女真语地名遗存。巴拉人的文化基因首先沉淀在蛟河及周边地区的地名之中,这些源于女真语的名称被称为“写在大地上的历史”,默默诉说着当年的聚落分布与生活场景。在蛟河留下了诸多独具特色的称谓,不胜枚举:窝集口,“窝集”在巴拉语中意为密林,此地因位于密林与沟河交汇处、是巴拉人日常活动的重要出入口而得名,直白勾勒出他们依林傍水的居住选择;半拉撮罗,“撮罗”是巴拉人传统的锥形窝棚,这个地名精准指向他们曾经的居所形式,成为追溯其居住文化的重要线索;额勒赫,意为“平安屯”,寄托着巴拉人对居所安宁祥和的期许;乌林沟河,得名于“富有”之意,想必是这条河流曾为他们提供了丰沛的渔产与生活资源,滋养了世代族人。还有以物产命名的少拉哈子,意为“山梨”,暗示着这里曾是山梨繁茂的富庶之地;以地貌特征命名的青背(浅河),简洁勾勒出河流清浅、山岭陡峭的自然风貌;拉法山的“拉法”为满语“拉佛”的音转,意为“熊”,因古时山中多熊、山峰嶙峋陡峭而得名,尽显山林的原始野趣。
多元交融的民俗活动。祭江仪式是巴拉人渔猎文化的精神图腾,他们将松花江视为神灵,感恩其馈赠,即便在特殊年代也未曾完全中断。
“打画墨儿”是巴拉人元宵节的独特习俗,源于一则感恩救火、祈求平安的传说:正月十五、十六两天,不分辈分可相互往脸上抹锅底黑灰,祝愿对方全年平安如意。
在娱乐与社交方面,巴拉人有独特的集体舞“巴拉莽式”(又称“野人舞”),为满族“玛克”(舞蹈)的一种。每年春季祭天、祭山仪式中萨满跳神完毕后,男女青年赤膊披发表演,男舞者穿豹皮裙、持手铃,女舞者穿柳叶裙,舞蹈原有八段,现存“开门红”“满堂红”等五段,直至深夜方休。
巴拉人的劳动歌谣同样鲜活,记录了渔猎生活的点滴,如《大风天》唱道“大风刮得直冒烟,刮风我去打老虎,打个老虎做衣衫”,《大雪天》描述“黑貂跑到锅台后,犴子跑到房门前,抓住黑貂扒了皮,色克(貂皮)正好做耳扇”,还有《犴子高》《大踏板》《拉大网》等渔猎歌谣,成为传承文化记忆的口头载体。
以萨满教为核心的宗教信仰。萨满教信仰贯穿巴拉人生活始终,同时也融合了佛教、道教元素,民间还信奉狐、黄鼠狼、蛇仙、貂神、虎神、树仙、石仙等,其居住地常有命名的神树、神泉、神石、鬼谷,还建有狐仙堂、山神庙,宅院刻有独特图腾,彰显神秘的信仰体系。
从深山遗珍到文旅融合的新生
巴拉人并非独立民族,而是明末女真的部落分支,因长期与外界隔绝,其独特的祭祀文化、渔猎文化、生活习俗、语言歌舞等得以完整保留,成为满族原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女真文化最后的活态遗存,对研究女真各部习俗、补充满族历史文化具有特殊意义。
如今,为保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蛟河市实施了市博物馆展陈宣传、前进乡张广才岭原始森林游、富江村祭江河灯节等活动形式,推动巴拉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从深山密林的渔猎部落到文旅融合的文化名片,蛟河巴拉文化历经数百年沧桑,始终坚守着女真先民的文化根脉。那些流传至今的习俗、地名与技艺,不仅是吉林东部地域文化的宝贵遗产,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生动见证,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中,持续书写着不朽的文化篇章。
参考文献
穆晔骏:《巴拉语》,《满语研究》1987年第2期
穆晔骏:《居住在张广才岭的满族“巴拉人”》,《北方文物》1984年第2期
李果钧:《吉东满族“巴拉人”习俗》,《吉林满族》1991年
李可漫:《巴拉人〈小莫尔根逸闻〉的采录》,《恰喀拉人的故事・小莫尔根轶闻》(吉林人民出版社,2019)
张林、孙颢:《长白山“巴拉人”生活与文化习俗考略》,《满族研究》2012年第2期
朱立春:《满族说部文本研究》长春出版社2016年
蛟河市政府、关云蛟:《巴拉文化》蛟河市人民政府官网2016年
( 作者:于永斌 ,蛟河市文物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