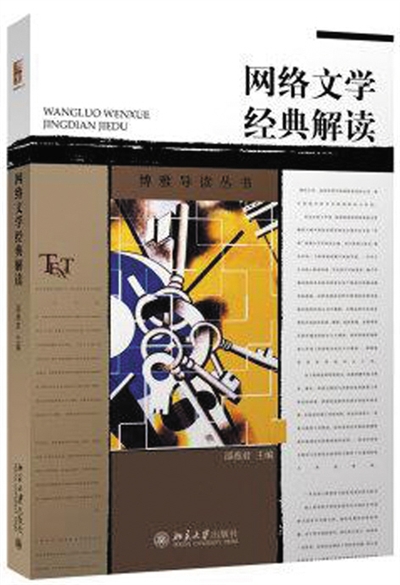
偶遇“孤本”
成为“猫腻粉丝”给“网文大神”写颁奖词
如果不是偶然读到网络“大神”猫腻的《间客》,仅凭一颗“初心”闯入网络文学世界的邵燕君,也许很快就要遭遇另一次“绝望”。这部让邵燕君拿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作比的网络小说,在玄幻的背景下讲述了一个小人物许乐的成长故事。
与同类型作品的主人公不同,许乐不会为自己和亲人的利益不择手段,而是始终在人类终极关怀的意义上遵从着道德良心的要求。这种让作者猫腻津津乐道的“情怀”,在邵燕君那里成为“启蒙主义精神在网络时代的一种回响”。
猫腻的作品质量为邵燕君提供了研究网络文学的信心,更为关键的是,“猫腻粉丝”这一身份让她拿到了一张进入网络文学讨论的“入场券”。
初来乍到时,面对网络小说陌生的黑话系统、繁复的类型和多变的文化构成,邵燕君很快认清了自己的“外地人”属性。相比自己开设的网络小说课上那些本是资深粉丝又正在接受学院教育的学生,她处于不可避免的劣势。
邵燕君承认,自己至今阅读的网络小说量也不大,真正欣赏的作品不多。猫腻“逆流而上”的作品难得一见,几乎可称“孤本”,也成为她的“救命稻草”。而这种巧合而成的粉丝关系,也在“学者粉丝”这一身份中埋下了内在的矛盾。
她在《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中对猫腻的论述,与她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中对毕飞宇、杨显惠等传统小说家的评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她形容猫腻“小说的调子恢宏而明朗”,分析的重点落在猫腻的“情怀”,并由他对人的关注衍生出两个副命题:独立人格的自我实现和对人生意义的积极肯定。
在网络小说庞大创作量的背景下,这种分析显得过于“奢侈”,不太可能成为处理网络文学的“常规武器”。而出身“草根”的猫腻经由精英学者的阐释已“登堂入室”,他以金庸、路遥和鲁迅为文学偶像的信息,更塑造了其小说贴近新文学的形象,与网络文学已不处于统一文化阶层。这样的猫腻,还能代表网络作家吗?如果不能,邵燕君的“粉丝”身份也将随之瓦解。
更为有趣的是,在第二届“腾讯书院文学奖”颁奖前夕,邵燕君在与猫腻面对面的访谈中为他读了自己所写的“完整版授奖词”。虽然对猫腻口称“猫大”,但邵燕君身为精英学者,除非完全放弃拥有授奖资格的“精英”立场,很难与自己的“大神”形成普通“粉丝”与“大神”间的单纯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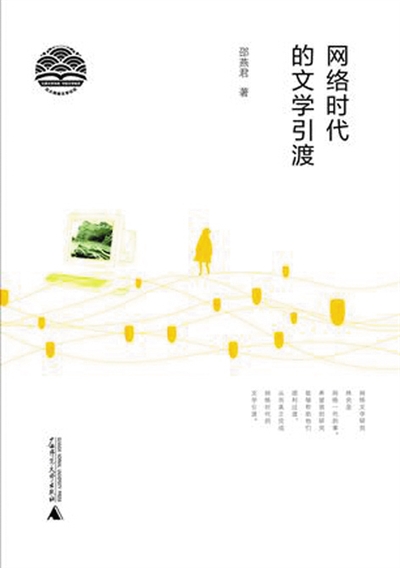
错位导向
立足精英立场欲“文学引渡”
努力成为“学者粉丝”的邵燕君,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学院派的精英立场。这是她的精神来源,也是她的立足之本。选择猫腻,根本原因是因为他的作品符合自己的文学品味,能够欣赏。开设网络小说课程,是为了训练学生们的学术能力和理论修养,让这些资深粉丝能够把网络上的“土著理论”和民间话语体系,翻译成凝练准确的学术语言。
然而,谁真正需要这种欣赏和翻译呢?不是网络小说写手,不是网文读者,而是精英本身。
邵燕君对网络时代的设想,是形成一种“以精英为导向”、“精英”-“草根”良性互动的主流文学。作为学者,她和她理想中“学者粉丝”们的工作,就是重建一套精英取向的标准评价体系。以这套评价体系渗透到网络文学的创作中,实现“文学的引渡”。
需要“引渡”的是包括对中国古代和西方的反叛、继承和革新的新文化传统,这恰恰是当下网络文学屡屡绕过的文化资源。提醒她注意到这一点的是当年课堂上的学生、现在达特茅斯大学任教的谢琼。她曾问道:当我们责备“网络一代”过于现实功利、缺乏理想激情和崇高美感的时候,有没有反思过是谁把这样一个精神荒芜的世界留给他们的?
这个问题让邵燕君很受震动。她认识到,相比于躲进“纯文学”理想与美感的自我陶醉中,消极地忽视和否认网络时代的到来,反而不如在随波逐流中“暗渡陈仓”,才更有担当。
据她的了解和观察,网络文学的3亿用户,“都是由网络文学‘唤’回的读者。即使网络文学不好看了,也别指望他们去读传统主流小说。”而这3亿读者,是精英学者不容放弃的启蒙对象,他们为此必须想尽办法,哪怕乔装“粉丝”,以退为进。
以“学者粉丝”的身份进行“文学引渡”,是邵燕君研究网络文学六年中最重要的成果,而其真正服务的对象却非网络文学,而是精英学者。引渡者自渡,邵燕君与新文化传统同生同灭的一代学院精英,搭上了通往网络时代的“诺亚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