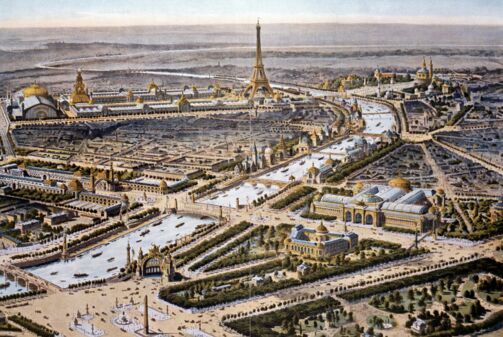
对巴黎的认识最早可追溯到罗马皇帝朱利安的记载,在他的记忆中,巴黎是一个叫卢特提亚的小镇,其罗马名字是巴黎,那里阳光明媚,盛产美酒。然而直到启蒙运动之后,原本籍籍无名的巴黎才焕发出勃勃生机,逐渐声名远播。18世纪,影响深远的法国大革命(1789-1794)既给巴黎民众带来了民主与共和的希望,也让整个巴黎城陷入了血腥动荡的政治纷争。几年之后,巴黎迎来了法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领袖拿破仑·波拿巴。从此,法国结束了自大革命以来的混乱状态,开启了一个灿烂辉煌的19世纪。
巴黎神话
19世纪的巴黎经历了频繁的政坛更迭,从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4)、波旁王朝复辟(1814-1830)、七月王朝(1830-1848)、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1852)和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直至世纪末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
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法国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法国也进入了现代性的萌芽阶段。对于这段历史,马克思做过这样的评价,“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它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人民的反抗最终酿成了1830年巴黎三天的暴乱,也就是历史上“光荣的三天”。1830年的这场革命虽然迎来了“资产阶级君王”路易·菲利普,摧毁了巴黎城中所有与波旁王朝有关的皇家象征,但是却并没有造就资产阶级所梦想的共和,在七月王朝统治下,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社会当权地位,王朝的命运在新的国王手中得以延续。除了菲利普,巴黎是这场暴乱的另一位受益者,它因为帮助菲利普建立了七月王朝而获得了王室的青睐,国王不仅盛赞在“光荣的三天”中英勇战斗的巴黎战士,还公开宣布巴黎是他的故乡。
有关巴黎的书写虽然早在15世纪初已经萌芽,但是直到19世纪才达到巅峰。19世纪前半期,巴尔扎克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忠实记录了波旁王朝复辟和七月王朝的历史,其中他所创作的《人间喜剧》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在这部作品集中,巴黎不仅是巴尔扎克安置众多人物的世界,也是他记录19世纪前半期巴黎风俗史的日志。在哈维眼中,巴尔扎克的巴黎史描写的是“现代性的神话”,对此,本雅明也曾表达过相同的意见,他将巴黎视为巴尔扎克的“神话学繁殖地”。列维·斯特劳斯曾将现代性神话视为一种想象的结构,这种结构将各种冲突呈现为令人惊诧的异质性。巴特则将神话视为有关现代性起源和发展的叙事,这一叙事通过展示貌似真实的虚假画面来遗忘历史。就此,无论是前者想象的物化还是后者人为的现实,神话都是一种目的性的结果。哈维曾明确指出,巴尔扎克的作品展现的即是作为神话的现代巴黎是如何构成的。
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现代巴黎的神话主要是通过外省人在巴黎的奋斗、成长和体验来传达的。在19世纪的法国,巴黎和外省是一对彼此依存又相互冲突的存在,虽然两者同时经历了现代化的过程,但巴黎作为财富、文化和权力的中心,对外省青年所产生的诱惑难以抗拒。在这些城市外来者之中,拉斯蒂涅堪称巴黎征服者的典型代表。作为外省没落贵族的后代,他不仅迫切地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强烈地渴望拥有财富和权力,在巴尔扎克笔下,他属于最终成功晋级为巴黎资产阶级新贵的幸运儿。以这样一个怀揣梦想的外省青年在巴黎成功攀爬到上层阶层的经历,巴尔扎克将19世纪前半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风尚描述得淋漓尽致。在某种程度上,拉斯蒂涅的成功与巴黎社会当时习俗的变化有莫大的关系,“在19世纪前半期的巴黎,社会习俗也正经历着一种重大变化——‘出生’这个古代政制中评判社会身份的唯一标准被‘金钱’这一新的普遍性社会所指代替”。在这个过程中,蓬勃兴起的巴黎资产阶级不仅意味着阶级结构正发生着变化,也预示了金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巴尔扎克的时代,贵族阶层虽然日渐衰颓,但是门第依然是打开巴黎上流社会之门的第一把钥匙,拉斯蒂涅能够成功进入巴黎上层社会,最开始也是依靠他的阶层,然而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单凭门第本身并不能保证拉斯蒂涅的成功,在金钱的步步紧逼之下,门第不得不节节败退,正如鲍赛昂夫人最终败给了暴发户家的小姐洛希斐特。在巴黎,金钱正在成为社交界声色犬马生活的最终保障,成为巴黎神话构成的隐秘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