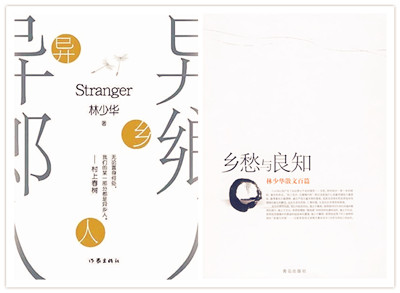
林少华作品
“翻译任何作家作品没有像翻译村上作品那样得心应手”
从2001年开始,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始出版村上春树的书。沈维藩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文学编辑,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的43本书中有36本是他做责任编辑的。他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上海译文出版社林少华译的村上作品已印制870万册。他评价林少华是“真正的翻译家”:“一般的翻译家是亦步亦趋的,但是林老师翻译的文学作品是在看懂的基础上又充满变化。”
林少华翻译的80多部日本文学作品中,有一半是村上春树的:“翻译任何作家没有像翻译村上春树一样让我觉得开心,得心应手,有一种配合默契的感觉。翻译最愉快的感受是自己在倾诉,不愉快的感受是只能听别人在倾诉。产生共鸣的时候,不知自己是作者还是译者,但这不意味着我乱来。只不过我们对人、事物、景物有这种微妙差异产生的平凡美的捕捉是很相近的。”
事实上,被大众忽略的一点是,村上春树也是翻译家,并且他翻译的量和创作的量相当。村上春树翻译了雷蒙德·卡佛全集、《麦田守望者》、《了不起的盖茨比》 等美国文学作品。林少华见过村上春树两次,两人也交流过翻译:“关于翻译,村上有个观点,他说翻译,哪怕是稍有一点变通修改,只要读起来顺畅有趣,就是成功的翻译。他甚至说,翻译最需要的是语言功力,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充满偏见的爱,只要有了这点,其他概不需要。”
谈到村上春树对自己的影响时,林少华说:“我‘邂逅’村上时已经三十六岁了,村上时年三十九。两人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都已包上了一层足够厚且足够硬的外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说有影响,主要集中在某种感悟和修辞。”
林少华说的“感悟”和“修辞”分别指的是觉得美和表达美。“觉得美”是指两人对生活中的平凡美感悟相似,“表达美”是指不仅要能感悟出来美,还要用修辞的手法表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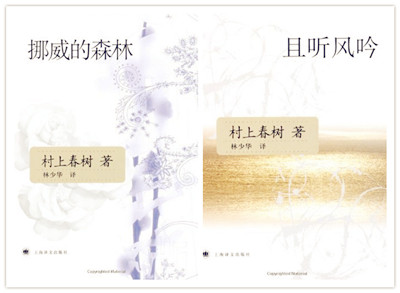
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的作品(网络截图)
村上春树30年来文学创作的主题和方向,林少华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9-1994年是村上春树创作第一阶段,如 《且听风吟》 《挪威的森林》,通过描摹刻画城里年轻人的孤独感、无奈感和疏离感,从诗意角度拓展城里人的心灵处境。1994年,从《奇鸟行状录》 开始,村上的文学创作进入第二阶段。《奇鸟行状录》 《海边的卡夫卡》 和 《1Q84》 第1部、第2部等作品中,村上开始将笔锋指向日本黑暗的历史部位和“新兴宗教”这一现代社会病灶,表现出追索孤独的个体同强大的体制之间的关联性的勇气。
“但这个转变不是一下子转变,任何一个东西转变都有个过渡阶段,只是到这个时候表现得更明显。前15年,村上春树关注人本身的问题,通过诗意开拓人的心灵处境,使孤独感、疏离感得到某种抚慰和释放。1994年开始,村上春树开始关注人与体制。用村上的说法就是‘鸡蛋’与‘高墙’之间的关联性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是一个‘鸡蛋’,有我们面对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1994年前的作品是通过孵化发掘鸡蛋内部的主体性、灵魂的尊严,而1994年后的作品则是通过‘鸡蛋’与‘高墙’之间的碰撞,人与体制的冲撞,来发掘人如何保持主体性、灵魂的尊贵性。”
林少华认为村上春树对“人与体制”的关注是其作品最难能可贵的一点。“遗憾的是,中国人主要的阅读倾向还是前15年的,以 《挪威的森林》为主,而后15年对村上的文学转向关注不多。因为中国文学作品宏大叙事多,对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阐述比较多,所以对村上转变后的这部分作品关注不是很多。”
《奇鸟行状录》 是林少华最喜欢的村上春树作品,林少华称这本书里什么都有:“1993年到1996年我在日本长崎县立大学教中国文化,在那个期间,我翻译了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回国之后翻译了后半部分。不管怎么说 《奇鸟行状录》 是村上写作一个跨度极大的转变。文学作品光是主题思想有趣,还不足以吸引人。这本书里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结构的变化和语言表达上的力度,比他以前的作品都上了一个台阶。”
《奇鸟行状录》 里有比较多的血淋淋场面,但林少华表示,这也是一种审美,一种陌生性的审美:“完全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世界,给你一种崭新的感觉。村上春树的文学想象力在这本书里达到淋漓尽致的地步。看了这部作品,再看其他作品都觉得黯然失色。”
对于读者“我们看的不是村上的作品,而是林少华的作品”的评价,林少华表示:“从翻译角度来说,也并不能说这种说法就过于偏颇。因为翻译是‘二米饭’,换个说法是,翻译是原作者和译者两人结婚生的孩子。读者不是用日文读村上春树,而是用中文在读村上春树,其实他读的已经不是外国文学意义上的村上春树了,而是翻译文学上的村上春树。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又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不是一回事。一个相对优秀的译者对原文的把握在普通读者之上,有人说直接读原文就好了,其实这是一种认识误区。译者首先是个读者,而且是个深度阅读的读者。他所传达出来的东西比一般读者要高一些。”
说到这里,林少华提到他的同龄人王小波对翻译的理解:“王小波曾说他文学上的‘师承’得益于查良铮先生译的 《青铜骑士》 和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并说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
优秀的翻译家都是“文体大师”,在这一点上,林少华觉得和王小波不谋而合:“有一次我自吹自擂,我作为翻译匠的贡献不是提供村上讲什么故事,而是提供了一种村上式的修辞,这就丰富了中国汉文学在艺术上新的表达可能性。翻译村上的也不止我一个,别人传达的大体是故事,我传达的是一种修辞方式。其他人翻译的和任何一个日本作家可以混淆起来,但是我翻译的村上是这一个不是那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