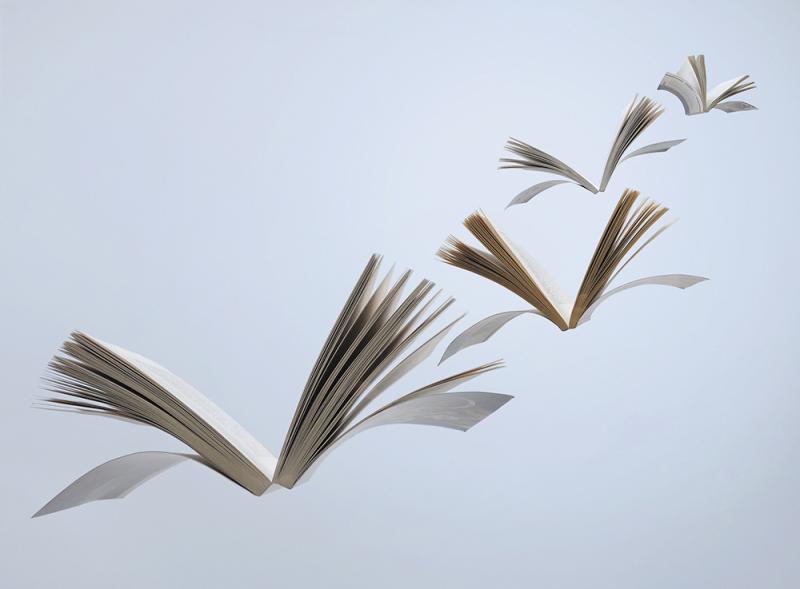
究竟有没有一条我们自己理出来的,概括出来的,可以说得清楚的那个传统?
徐芳:把评论的事做到极致是怎样?据说就是一种情怀?您的文章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理论评论奖,印象中获奖的多是砖头厚的专著,而你这篇《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是以一万多字的单篇文章获奖,这说明了什么?
张新颖:这个大概不能说明什么,不过是个形式问题。书有书的好,文章有文章的好。以前理论批评奖里面,获奖的有书,也有单篇文章,虽然单篇文章比较少。
徐芳:你说过“要说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恐怕就是,因为我多年从事沈从文的研究,我以沈从文为个案,描述了现代和当代文学之间密切联系的一条脉络。”但有人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为什么理论评论要解析经典名作、经典作家呢?是否所有历史上的艺术、文学研究,都必须和当代相结合?
张新颖:不是说所有历史上的艺术、文学研究,都必须和当代结合,而是说,我们在当代,不能假装我们这个当代是凭空产生的,或者可以孤立存在,和历史不发生关系;当代的创作,也不可能和历史上的创作不发生关系。
我做现代文学研究,一个很深的感想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最近的文脉就是现代文脉,或者换个说法,是我们现代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其实已经超过了用“重要性”这样的词来描述。怎么说呢?不论我们承认不承认,意识没意识到,我们都是一个现代文学传统,或者说是现代文脉的承受者。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这样讲话,为什么这样写作,就有一个最基本的现代汉语的问题。但现代汉语的文学历史,也不过是一百多年的时间。我们不能以为现代汉语这个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一个最近的创造过程中才逐渐产生的,这里面当然不是一种力量,但是最重要的一种力量,就是现代文学的创造力量。
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东西完全无知的话,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所以我想多一点自觉,总比少一点自觉好。就是对这个文脉多一点感受,总比少一点感受好。
现代文脉这个东西,不是一条一脉,也不固定。我们会把一些东西固定化,把一些东西给它命名,但究竟有没有一条我们自己理出来的,概括出来的,可以说得清楚的那个传统?有否那一条线,有否那一脉,其实我是很怀疑的。这些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大家也知道,其实在现代的起点上,汇入很多很多的声音,但就是这个众声喧哗的宽阔局面,也慢慢变得狭窄了。
我们在讲文脉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它固定化、概念化,不要相信概括出来的东西,要由我们自己去体会。有的传统,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还有一些传统一下子看不到,那个脉它是比较隐藏的,但那个比较“隐”的脉,它一定是比“显”的不重要吗?这个也不一定。
还有一点我想说,作为一个今天的人,我们不要害怕传统文脉,怕那个东西会掩盖且抹杀掉我们的创造性。我想应该有一点勇气,比如说像当年的艾略特,他讲个人才能和传统的时候,他说儿子发明父亲。当艾略特老了的时候,他也会反省这个说法,但儿子发明父亲,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现代文学传统,就是我们那个遗产,到底是不是有价值的,这个不仅看遗产本身,还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把那个传统激活,去从那里面发现有价值的部分。
所以这个不是考验传统,而是考验我们自己。有的东西就是了不起,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比如说撞钟,有些人撞不响,有的人力气小,回响也就比较小;有的人力气大,就很响。
其实是考验我们自己的力量,包括我们自己的创造力,有创造力才能够把这个传统激活,才能够从这个传统里面发现更有价值的东西——你如果真的能够把它激活。真的有所发现的话,再用文脉这个词来讲,比如说我们找矿,找到了一个脉,就了不得。所以,如在个人的创作上,为自己找到一个脉,这个脉并不受任何专家学者指引,而是你自己去找到的,它就能够给你提供力量,更可以持续地支持你不断创造。
我描述沈从文传统在当代创作中的回响,其实有上面说的这么个思想背景在,所以我说是一个个案,一条脉络。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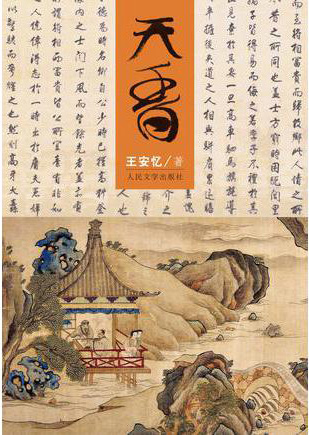
“气数”和伟力,造就繁华的上海
徐芳:你曾和王安忆做过大量关于创作的对话,她倾尽心血去写,也写出了极大的分量。我认为她的作品里“物”的形象十分鲜明,就以《天香》为例,你认为《天香》中的“物”,与罗布·格里耶所状写的“物”有什么不同?在格里耶那儿,“物”与“人”一样,可以成为作品的主体,“物”是与“人”并列的一个中心。王安忆笔下的“物”与中国古代的“物”之间,有没有某种传承关系?
张新颖:太不一样了。罗布·格里耶的“物”是要和主观的感情投射隔离开来,《天香》里的“物”——顾绣,她叫做“天香园绣”,却是载体、中介、创造物,不仅和小说里的人物不可分割,而且和小说叙述者的认识、感情紧密关联。而且我觉得《天香》好,就好在这个“物”聚集了很多东西。
王安忆多年前留意顾绣,不论这出于有意识的选择,还是无意识的遭遇,现在回过头去看,是预留了创作拓展的空间。如果说这一物件选得好,就因为自身含有展开的空间,好就好它是四通八达的。四通八达是此物本身内含的性质,但作家也要有意识地去响应这种性质,创造性地写出来才行。
“天香园绣”这个物件,有几个“通”所连接、结合的丰富层次:
一是自身的上下通。“天香园绣”本质上是工艺品,能上能下。向上是艺术,发展到极处是罕见天才的至高艺术;向下是实用、日用,与百姓生活相连,与民间生计相关。这样的上下通,就连接起不同层面的世界。
还不仅如此,“天香园绣”起自民间,经过闺阁向上提升精进,达到出神入化、天下绝品的境地,又从至高的精尖处回落,流出天香园,流向轰轰烈烈的世俗民间,回到民间,完成了一个循环,更把自身的命运推向广阔的生机之中。
二是通性格人心。天工开物,假借人手,所以物中有人,有人的性格、遭遇、修养、技巧、慧心、神思。这些因素综合外化,变成有形的物。“天香园绣”的里外通,连接起与各种人事、各色人生的关系。“天香园绣”的历史,也即三代女性创造它的历史,同时也是三代女性的寂寞心史,一物之产生、发展和流变,积聚又融通了多少生命的丰富信息!
还有一通,是与时势通,与“气数”通,与历史的大逻辑通。顾绣产生于晚明,那一时期人对生产技术的认识与掌握已进步到自觉的阶段,“天香园绣”也是顺了、应了、通了这样的大势和“气数”。
“天香园绣”能逆申家的衰势而兴,不只是闺阁中几个女性的个人才艺和能力,也与这个“更大的气数”——“天香园”外头那种“从四面八方合拢而来”的时势与历史的伟力——息息相关。放长放宽视界,就能清楚地看到,这“气数”和伟力,把一个几近荒蛮之地,造就成了繁华鼎沸的上海。
中国文学有缘“物”抒情的传统,王安忆的小说和古代“物”诗,未必有什么直接关联,但她写“天香园绣”通性格人心、关时运气数、法天地造化,其实也不妨看作是一种“抽象的抒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