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机会和新泉老师长谈了。
没想到,当年一别竟有16年之阔,其间只是在马尔康短暂一晤,未及尽兴又是另一程深不见底的分别。临别握手,张老师用了十分的力气,握一次,仿佛要顶得上10次。他说,这一别,此生不知是否还会再见,我立时就感觉泪水泉涌。说话时,他已年届80岁,仍然身体健旺、思维敏捷。虽然满头白发,却从骨子里散发出一股刚强之气,完全是一副硬汉风范——只有深情和深沉,而不感伤。他微笑着,转身离去。
有一天,他突然从成都打来电话,说他将出此生最后一本诗集,真正的收官之作。他这样说时,我觉得此事确实非比寻常,但以他的身体和写作状态,还真就未必就能“收官”。这一本出过之后,用他自己的判断“已是资深老年,却迟迟未能痴呆”,每逢文思泉涌之时,不把那些想法和感悟变成新的诗行,难道还要像灭火一样,硬把它们从思维中压灭吗?
他说他想了又想,还是想让我“在这本书前写几个字”。我当时诚惶诚恐,他老人家说得轻巧,可在一本书前能随便写字吗?那叫序呀!我何德何能竟敢在一个前辈名家的书前班门弄斧呢?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能写,可是张了几次嘴,那个不字还是没有说出口。
虽然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在一位前辈面前指指点点,但同时更没有理由和勇气拒绝一位宽厚长者的信任。细想,像新泉老师这样的大诗人、资深名家,已经不需要再找一个什么人为自己诗集写序撑门面了,甚至也不需要出一本诗集来刷自己的存在感了。如果说他出这本书是为了留个纪念的话,找我写这个序也不过是为了留个念想吧!为了我们许多年的彼此关注和一份叫做缘的忘年情谊,或许真的不应该拂了他这片美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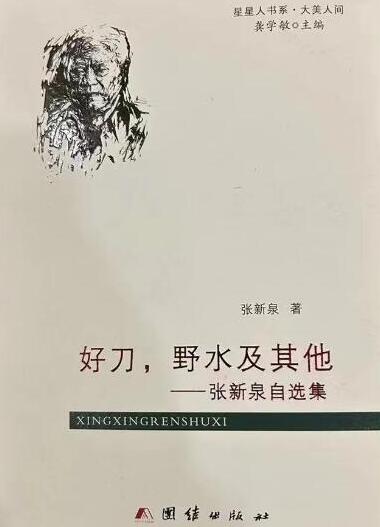
新泉老师在《缘分》一诗中说:“缘分不一定大红大绿/鼓角之外,最深长的是/细细的洞箫/我就这么一点点清水/和一份永远的歉疚/你千万别开出花来/吓我一跳”。我想,此刻用在我身上正合适,他的这个想法真的吓了我一跳。好在我还懂得,随顺长者的心意是最大的真诚和尊敬。那我就从命而为吧!认真拜读一下这部诗集,倾听他对人生、世界以及诸般事物的认知、理解和态度,谈谈自己的收获和心得,权当和他老人家做一次促膝长谈了。这也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雅事和幸事。
还记得多年之前,第一次去成都拜访新泉老师时,他随手给我带来一本《张新泉诗选》。书不厚,选诗也不算多,却字字玑珠,仔细品读,很有一种舍不得一气读完的感觉。但不管如何不忍,还是很快读完了。因为感慨万端,不吐不快,便不由自主地写了一篇解读式的短评。从此,很真切地视张老师的诗为宝贵,每得必认真品读。
后来,有一次去曲有源老师家做客,偶然发现他家的书架上有新泉老师的另一本诗集《宿命与微笑》,书的扉页上还有他的亲笔题赠:“我一生的努力,就是向宿命微笑”。很意外,也很兴奋,当时就向曲老师提出了借阅的请求。由于曲老师也没有明确提出归还日期,诗集就在我手里一直“借阅”着。
又一次去曲老师家吃饭,突然想起来这本没有归还的诗集,口是心非地说哪天一定要归还。曲老师则看透我的心思,哈哈一笑,很大方地说:“既然你很喜欢,就转赠你吧!”就这样,延宕多年之后,此诗集竟然易主成了我的。
翻阅这个新选本《好刀,野水及其他》,我发现当年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一些诗,比如《关于底气》《骨子里的东西》《撕》《枪手》《好刀》《好狗》《拉滩》等篇什竟然都赫然在列。也就是说,我曾为之痴迷的那些诗,张老师自己也很喜欢。欣喜、快慰之余,却忍不住在心里问一句:为什么会这样?
想来,这也不仅仅是审美标准的问题,更主要的,可能还与审美趣味和精神取向有关。虽然我和张老师出身和经历不尽相同,但世界观形成的年代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个人的性情以及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也大致相同,所以在艺术和心灵上容易发生共振。张老师的人生起点比我高很多,我是纯粹的农家子弟,贫农,穷人;他不是,他是地地道道的富家子弟。他爷爷曾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有土地还有商号,家财万贯。遗憾的是,他爷爷的财富不但没有成为子孙们的福荫,反而罹祸。
少年时,张老师就读于富顺二中。那是一所创建于清朝末年的老学堂,李宗吾曾做过那里的校长,学校的教学传统和教学质量均好。加之少年张新泉天赋过人,聪颖灵通,早在初中时代就已经开始在《少年文艺》《工人日报》和本县的《富顺报》等报刊发表诗作,一时成为远近闻名的小人物。
多年后,他敢说,他一生的努力都是向宿命微笑。当他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时,他还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还无法向厄运微笑,那时他只能哭。辍学后,为了谋生,这个曾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像是一匹失群的马驹,不得不闯荡、行走于社会底层。20多年间,他做过筑路工、船工、码头搬运工、锻工、剧团乐手、文工团创作员、地方刊物编辑,历经劫难,九死一生。
值得庆幸的是,经历了种种艰辛、磨难和种种摧折、锤炼后,他并没有被摧毁,主观上也并没有颓废,没有成为一个胸中只有仇恨、怒火、怨尤和负能量的废物。浴火重生后,呈现于人们眼前的是一个豁达、开朗、朴素、深沉、智慧、幽默、重情重义、心怀悲悯、格局宏阔的优秀诗人。他一生受过的苦和欺压、屈辱以及一生帮助、接济过的人、结下的善缘、播下的友爱、创造的种种功业等等,在这里,我想,都不必一一细说了,凡对他有所了解的人都心口皆碑。总之,他终究没有成为一堆没筋骨、不成器的烂铁,而是成为了他自己笔下的那把好刀——
好刀不要刀鞘
刀柄上也不悬
流
苏
凡是好刀,都敬重
人的体温
对悬之以壁
或接受供奉之类
不感兴趣
刎颈自戕的刀
不是好刀
好刀在主人面前
藏起刀刃
刀光谦逊如月色
好刀可以做虫蚁
渡河的小桥
爱情之夜,你吹
好刀是一支
柔肠寸寸的箫
好刀厌恶血腥味
厌恶杀戮与世仇
一生中,一把好刀
最多激动那么一两次
就那么凛然地
飞 起 来
在邪恶面前晃一晃
又平静如初……
人类对好刀的认识
还很肤浅
好刀面对我们
总是不发一言
——《好刀》
终于,在43岁那年,他时来运转,在文学的殿堂里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历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星星》诗刊副主编、常务副主编、编审。1985年出了第一本诗集。自那时起至今,他一共出版14部诗集。14部诗集,就像14根高大的柱子,支撑起他诗歌艺术的大厦,也支撑起他精神世界的穹窿。这14本诗集,我并没有一本不落地全部阅读,但就从我看过的几本诗集说,似乎他的每一本诗集都承载着他作为诗人存在的全息。读任何一本,都能比较全面地获取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信息和气息。
《宿命与微笑》是他1994年出版的诗集,很早啦!重读其中的作品,甚至让我感到吃惊,你看他26年之前的叙事手法和能力,其意识、其语感、其技巧、其密度和诗性的自觉,就连现在最活跃的诗人中也没有几人能与其比肩。仅以开篇第一首《关于底气》为例:“……底气是另一回事/底气在丹田以下/沉稳、结实/对上述日常活动/从不参与/底气丰沛的人/常在谷中散步/随手摸摸树上的文字/花就开了……” 如此充盈、富足,这文学的底气和生命况味,到底从何而来?当然,这些无疑都是来自于他的生命本身。
什么叫宿命呢?就是你这一生的程序早已经被编排得丝丝入扣、天衣无缝,雷打不动。什么时候该你受苦,什么时候该你享福,什么时候该你倒霉,什么时候该你辉煌,都已经安排妥当。是有因才有果吗?不,也许是由果而设因,或者因果互生。不要说苦难出诗人,也许一个命里注定的诗人,就是要经受常人无法经受的坎坷与苦难。
当我们读到《撕》,读到“纸屑会再度变成纸/再度与你相逢时/一些化不掉的字/保不准会活过来/咬你”你就会知道,他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记恨那个时代的荒谬;当你读到《枪手》,读到“把人心与准星攥成一条线/枪,就响了/手一生,就说这么/一句”你就知道,他已经没有必要去抱怨人生的不测与凶险;当你读到《拉滩》,读到“轮到我们骂时/我们只仰躺着喝酒/仰躺着,把匍匐报复”你也就知道,他已经没有必要对曾经的苦难耿耿于怀;因为所有伴着疼痛揉进肉体里的沙子,最后都幻化成了闪光的珠宝。
新泉老师说,一切都是宿命啊!我理解,这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诗人用一生的经验、感悟和智慧,向我们透露的一个人生秘密。
在新泉老师的提示下,我发现,就连某人与某人之间的相遇、相知和互信,似乎也带有宿命的色彩。在那么多的诗人中,我为什么要专程拜访了他?拜访也就罢了,怎么那么巧,两人还真能谈得来?谈得来也就罢了,为什么还会有文学上持之以恒的互动和欣赏?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16年前我写下的一段浅薄小文,至今新泉老师还保留着。上次在马尔康见面,他特意用微信将那篇小文的图片发给我……感念之余,不得不对老先生的宅心仁厚和友善温暖的品性肃然起敬,可谓真正的良师益友也!
新泉老师嘱我写序,我理解,是在以另一种方式激励我。我虽然写了一些话在此书的前面,但仍然不能叫序,我只是为新泉老师这本新书打个场子,高喊一声大家不要错过了阅读的机缘。至于诗歌本身,我想,就不用我过多啰嗦啦。
好诗,谁都能读懂;好诗,谁读谁都有自己的领悟;好诗,好读者都会有公正、客观的判断。在这里,唯祝岁月虽老,新泉老师不老,他的诗不老,他还会以他的智慧和诗才继续给我们酿造出更加醇厚的诗歌之酒。
作者:任林举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来源:中国吉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