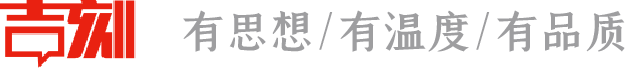教育几乎是每个家庭都极为重视的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早已不只是学生之间的战斗,许多家长纷纷选择“从娃娃抓起”,小学也随之变成了这场“教育大战”的主战场之一。
为了自家孩子能获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虎妈”“狼爸”齐上阵,致力于给孩子“打鸡血”,买学区房、上名牌小学、报课外班……由此“鸡娃”浪潮日益狂热。随着“双减”政策的施行,校外培训班、课外辅导班纷纷关闭,“牛小”的家长也打起了“地下战争”。
“赢在起跑线上”和“美好的童年”到底孰轻孰重?如何才能回归“育人”的本心?在急功近利的当下社会,怎样返璞归真?作家石一枫在最新长篇小说《逍遥仙儿》中围绕三个家庭的育儿征程,展现了北京“牛小”家长们的“内卷大战”,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北京众生相。
“我们”和“他们”:家长之间的“明争暗斗”
石一枫在《逍遥仙儿》中塑造了王大莲与苏雅纹两个“典型家长”形象。小说伊始,因游泳班“爆”了,王大莲在退“体验课”费用时遇到了麻烦,便顺走了“黄鸭子”,于是便有了“一只鸭子引出的纠纷案”,各色家长纷纷登场。最终,苏雅纹用一句“何必呢?人家也不容易”为王大莲救了场。
在石一枫笔下,王大莲粗门大嗓,一张嘴就挂相,面对各种生活常识、教育理念和乐理知识一概不知,由此遭到家长们的嘲讽和不屑,被壁垒分明地分成了“我们”和“她”;苏雅纹则是文静妈妈的代表,工作体面、会化妆打扮、善良有情商,一开始就是“妈妈群”里的“头儿”。
在家长们眼里,王大莲是粗俗不堪的,包括小张、苏雅纹在内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妈妈都会下意识地将顶撞博士班主任的王大莲和自己区分开,以表示和她的不同。“‘他们’就是针对‘我们’,看不起‘我们’。‘他们’虽不明说,可我都能感觉得到。在‘他们’眼里,我过去是个小偷,现在是个白痴。‘他们’成天把‘爱’呀‘同情’呀挂在嘴边,家里死条狗都像死了亲爹一样,怎么就学不会把‘我们’当人呀?”王大莲在遭受排挤后愤愤不平。
戏剧化的是,当王大莲在苏雅纹的蛊惑下,终于将自己家的“半扇楼”打造成“地下”辅导班时,王大莲就和苏雅纹成了“我们”,那些没有进辅导班的学生家长就成了“他们”。这些“小群体”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在不同的情形下是按照“身份”或“利益”划分的。
“芽芽”的爸爸庄博益在谈到以苏雅纹为代表的“小群体”时感叹:“在苏雅纹的语境中,使用了一个新的标准,重新划分了‘他们’和‘我们’——那个‘他们’是爸爸、丈夫,还包括了所有男人;对我来说,她口中的‘我们’却是‘她们’了。新标准支撑了苏雅纹的新策略,苏雅纹将一种对抗转化成了另一种对抗。”
评论家刘秀娟在阅读这本小说时,常会不自觉地代入自我,思考自己到底属于家长中的哪一个阵营。她认为,石一枫的小说看似是教育话题,但实际上内在的本质还是探讨人本身的问题,“小说当中不断出现我们、他们、你们、咱们,而这之间并没有清晰的边界,他会随着事情的发展在不同场域、不同场景、面临不同对象的时候,不断被打破、重组。”
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
带孩子、“卷”孩子、接孩子这些事,在石一枫看来对于任何一个有孩子的家庭,尤其是北京家庭,已然成了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很多母亲在有了孩子后,便一切以孩子的生活、健康和教育为中心,丧失掉了属于自己的五年,甚至是十八年。“在孩子上大学之前,一些母亲的生活基本全都丧失了,什么也顾不了。在我们的生活中,评价一个妈妈成功不成功,有人认为其实就是看你把你的孩子养成什么样。”石一枫说。
除了作家,石一枫在生活中也是孩子的父亲,直言有些“爸爸是说风凉话,或者是看热闹的那种”。“作为妈妈自然会跟孩子有牵肠挂肚的感觉,虽然爸爸也很着急,但不同的是,爸爸的操心是社会面的。我家孩子妈妈在孩子这方面‘卷’得比我要深,我可以忙事业、工作,可以把烦心的事躲开,但是作为妈却是躲不开的。”石一枫说。
“育儿的问题最残酷的是对女性时间的剥削,很多时候你变成了一个母亲,而不是你自己。”作家张悦然认为,教育的话题和女性的话题相关度非常高。在谈及女性成为母亲之后的变化时,她提到了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女性在成为母亲以后会因为孩子的缘故而交朋友,这种友谊不建立在其它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只建立在孩子的基础上,“可能还会存在一种竞争”。
“成为母亲以后,很多女性被迫接受各种其它场域作为自己主要的生活场景,还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甚至把它变成比自己原先生活里任何事情都重要的事情。我会觉得其实教育背后折射出来的是这些女性的时间被浪费,她们的才华也会被浪费。”张悦然说。
刘秀娟认为,张悦然的话触及了小说的另一层主题,即“人本身”。小说看上去是围绕着三个家庭的教育展开,实际上更大的主题是对于“人”,对于每个人自我的成长,“这个小说还探讨了成人尤其是女性自我的成长,我们每个人,家长也有他自己的主体性在哪里?个人的自我的存在和空间在哪里?我们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
《逍遥仙儿》的背后有着“石一枫式”的温暖
“我落人中然自在,本是天上逍遥的仙儿……”
小说结尾,王大莲和父亲“道爷”在庄博益的斡旋下言归于好,选择重新回到乡下,过起仙儿般的逍遥生活。这样的结局似乎美好得有些不真实,但这个选择却符合《逍遥仙儿》的小说逻辑,是石一枫理想主义化的处理。
张悦然认为,当我们跳出来,不再是我们的时候,也许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路径。“在小说的结尾,王大莲的方式是离开,短暂的逃离,和现实有一个冷却和距离,这是石一枫在思考之后给出的一个解决方案。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有没有可能都像我们的主人公一样,能够跳出这个自我。”小说写现实,呈现现实,但写小说不负有处理“现实事务”的义务。对于结尾的处理,石一枫解释道,“《逍遥仙儿》解答的方式是从困境中暂时跳出来,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在一个未遂的状态下生活。生活往往在无数次的失望和未遂的状态下进行,如果我们对生活有这种基本的认识,我觉得对《逍遥仙儿》的结尾倒是能够看得比较通透。”
在刘秀娟看来,这样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结尾,恰恰是石一枫温情和宽厚的体现,“文学不是励志格言,也不是警示语言,其实很难提供非黑即白的答案,但是文学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写作过程当中,去书写了生命的过程和它展现出来的状态,包含着对人的关怀。它让我们思考,让我们每个人寻找自己的答案,我们在生活的洪流和漩涡当中,都在努力冲刷出属于自己的河道,这个东西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事情。”
“如何做个逍遥仙儿?这本书可能并不能告诉我们答案,但是至少看完之后可以让我们稍微放松一下,这也是一件欣慰、愉悦的事情。”张悦然表示,《逍遥仙儿》的背后有着“石一枫式”的温暖,小说的最后可以落在一个让人感到慰藉的地方,人和人最终会找到相同的部分,彼此认同,彼此谅解。(惠子月 谢宛霏)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