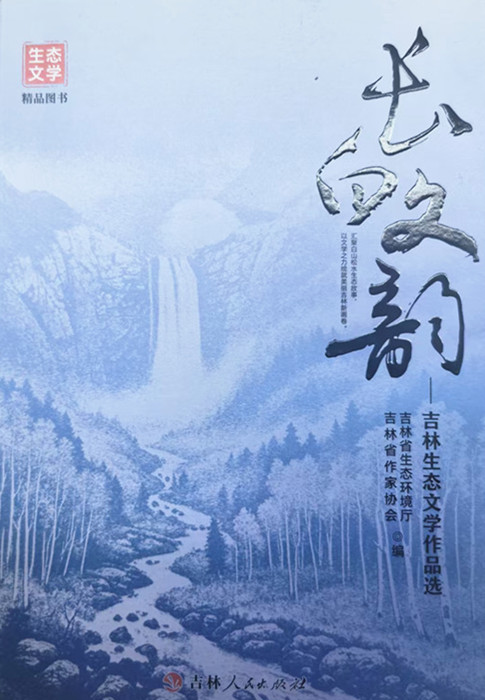
白山松水,大美吉林。近年来,吉林省生态环境厅与吉林省作家协会高度重视生态文化建设,携手推出生态文集《长白文韵》。该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倾力出版,以23万字、51篇佳作的篇幅,构建出一幅多维立体的吉林生态长卷。作品以记忆为经纬,将长白山的松涛、湿地的鹤影、黑土地的麦浪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生态画卷,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吉林大地的生态之美、守护之责、发展之变与文化之厚。它既是一部反映白山松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的见证录,也是一曲书写当地人民幸福生活的时代颂歌,更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进行了在地化、艺术化的诠释,重塑了人们对东北大地的认知方式与情感联结,展现出生态文学书写现实、触动心灵的力量。
小说:伤痕叙事下的生态觉醒
生态小说以多维镜像刺穿生存悖论,残雪将自己的小说称为“哲学实验小说”并提出,“读这种小说要破除思维的常规定势,用读者自己的生活体验去反复地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那种哲学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沟通。”比如王怀宇的《消逝的啾鸣》体现出一种折返,精神的溯源与淬炼。作者借“断趾麻雀”与“洞孔鸟窝”的微观劫难,将一则城市角落的生态寓言,升华为一曲关于生存代价、人性困境与现代性隐忧的深沉挽歌;谢华良的《秧歌湖》以儿童的视角凝视“敬湖仪式”与屯落搬迁的撕扯,让秧歌鼓点敲响文化记忆的裂痕;李金龙的《鸳鸯扣》则淬炼猎户“链马扣”为伦理试金石,当“放生土豹”的赎罪链条绞紧狩猎传统,东北荒野便溅起海明威式的存在主义血滴。
杨逸的《乌拉的故乡》以绿头鸭“乌拉”(满语“江河”)为独特视角,在松花江畔的风雪日常中,编织了一曲深沉的生命与文化双重寓言。杨逸以冷峻悲悯的笔调,借乌拉的际遇映照人类文化记忆、个体创伤与生命尊严的困境,将对“故乡”的诠释升华为灵魂归属、生命确证与文化呼吸的精神原乡。那颗沉入江底的心,终与“从天而降的河流”融为一体;李彤君的《“老等”向“南”呼唤》则让折翅苍鹭化身生态警务的寓言信使,镇南派出所“先锋班”的退役军人铁骨,在救护鸟羽的细琐行动中铸成生态文明落地的铿锵铆钉。吉林小说家惯以长白山为叙事支点,将松花江的波涛转化为文化诊断的手术刀,构建“小切口撬动大纵深”的思辨格局。然如李谦的《红箱子,绿箱子》等作的寓言锋芒稍钝,刻意符号消解了现实穿刺力——生态叙事真正的雷霆,终需在隐喻与真实的冰层下蓄积能量。
散文:草木山川的精神测绘
草木山川常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勾连起个人经验与集体记忆,吉林散文家以吉林生态为精神测绘图谱。在景凤鸣的《挂在边境的彩“链”》中,331国道化作缝合边地的金线,鸭绿江的史志考据与“白云搭救河水”的诗性共舞,织就家国血脉的斑斓通道;赵培光的《一路上有树》以树喻人,构建起“树—人—城”的生命共同体,其“看树是树,看树不是树,看树还是树”的禅意思辨,暗合孟繁华指出的“东北散文的玄学转向”。其散文在生态纪实中注入诗性智慧,形成事实与隐喻的双重奏鸣;格致的《草的阻拦》则以刺刺秧的微观抵抗,在苍鹭折翼的叙事褶皱里刺破城市化铁幕;张藩的《听松》解构季羡林的“二八妙龄”幻象,松涛三重奏完成对自然崇拜的现代转译;尚书华以“天问”体赋形圣山魂魄——天池为火盆上的水塔,岳桦成神性围巾,三江奔涌如离家的血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张顺富的《查干湖的春天》中的味觉书写:“苣菜的苦后回甘”“小根蒜的辛辣解毒”,将生态美学延伸至感官层面。这种“舌尖上的生态”与陈晓雷的《长白山三记》的视觉交响形成味觉与视觉的双重变奏;于德北借冰湖险陷与喜鹊筑巢,在裂缝中提炼“敬畏即生存”的法则;周云戈的《湿地人家的问候》笔下的牛心套保芦苇,从“西牛引水”的集体奋战到刘兴土蟹稻鸭的科技治碱,终以三代坚守重铸湿地精神的脊椎。
而王德林的《东辽河》以河长制缝合大地脉管,杨树的《云海之上》借偃松的贴地哲学与石海的时光包浆,共构生态思辨的双生塔——前者印证文明自我修正的伟力,后者昭示敬畏乃心灵永恒渡口。吴澍的《故乡的古榆树》告诉我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能让毁坏生态环境的悲剧重演;孙昱莹的《风过参乡》共塑吉林生态书写的多维向度,终凝成“天人共生”的深沉史诗;迟建边《滴台还是那个滴台》给人以过去到崭新的“滴台”之感;孙正连的《查干湖的精灵》等文本建立“历史—当下—未来”的生态责任链;伦理观上,陈凤华的《中华秋沙鸭的四季之恋》等篇目实践着“万物有灵”的叙事伦理;翟妍的《一道嫩江湾》与李万彬的《白鹤之乡莫莫格》亦是吉林西部朴素的生态乐章;莉璎的《应知故乡事》中“绿色粮仓”是“我”的故乡,“我”用毕生在亲近它的殷实 、壮美。散文章节的生态叙事亦完成对东北大地的精神测绘出山河的呼吸与人类命运的震颤,凝成白山松水的深沉史诗。
诗歌:自然咏叹的抒情重构
诗人应该是半个哲学家,平庸平淡没有诗歌可言。八位歌者有意地给出了自己对自然对人的探索,制造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象征,也竭尽全力从这象征中突围,展现自已独特的表达。任白的《岳桦之歌》以地质运动的暴力美学重塑岳桦生存史——“灰绿色军团”的战争修辞将植物群落升格为与火山、冰川对抗的悲壮军团。当“橙色血液”与“水晶城堡”相继成为毁灭性意象,岳桦的“蜘蛛铁足”与“匍匐满弓”却构建出更震撼的生存寓言:那些被解读为屈服的低伏姿态,实则是向死而生的战略韧性;龚保华的《长白交响》以地质纪年为轴,将造山运动解构为“冰与火的叙事诗”。而四季轮回被赋予相互响应的动态:春之飞扬是夸克级的生命躁动,冬之冰晶则是熵减定律的视觉证词。最致命的莫过于“林海合交响”的声学的有力回响。
王立民的《查干湖笔记》则以蒙太奇手法拼接渔猎、农耕与湿地保护场景,形成“生态蒙太奇”效果。当羊皮袄与冰层摩擦产生的静电,被写成渔把头与自然签订的隐形契约。马拉绞盘转动的不是渔网,而是黑土地的时间碰撞——那些被网眼过滤的晨曦,终将在冰窟窿里结晶成光的琥珀;潘占学的《长白山新赋》将“一山三江”的地理特征转化为“水塔—血脉”的意象群;艾力发的《流经故乡的江河》与孙超的《吉林行吟》两首诗构成互补的东北生态叙事——前者是毛细血管般的浸润式抒情,后者是时光扫描般的结构性凝视;艾力发的江河需要贴着皮肤倾听心跳,孙超的山水则要退后三步观看生态经脉。
报告文学:绿色发展的纪实样本
敏锐的时代洞察、书写现实样本,守护与表达那份源自“报告”的纯粹。比如,任林举的《家域》通过东北虎栖息地恢复的个案,以“红外相机影像”为实证材料,将科学报告转化为“虎—人—山林”的命运共同体叙事,借虎之“家域”为棱镜,折射土地认同、生存竞争、代际传承的永恒母题。黑夜虎啸刺破寂静,既是本能呼唤,更是孤独王者对存在意义的旷野呼告。当黎明微光收复失地,那渐远的吼声已刻入大地——所谓家园,实为生命以爪痕、气息与孤傲,在虚无中奋力划出的疆界,是一场确认自身存在的终极抗争。
张赤的《黑土流金溢远方》记录秸秆还田技术推广中的观念博弈,那些老农捏碎黑土的特写镜头,呼应着孟繁华强调的“细节的人类学价值”观念;赵连伟的《寻访东北红豆杉》的叙事尤为精巧。作者追踪一株雌株红豆杉二十年,记录其与几十米外雄株的“千年守望”,这种以“植物爱情史诗”的写法,让珍稀物种保护具有了《诗经》“蒹葭苍苍”的古典韵味;赵楠的《有形的翅膀》聚焦莫莫格湿地护鸟人,其“二十四小时人工护鹤”的细节尽显其热爱;李燕的《生态绿背后的铁汉柔情》通过生动细腻的笔触,成功塑造了基层环保执法者刘大俊的立体形象,兼具文学感染力与社会现实意义,是一篇主题深刻、叙事生动、社会意义突出的作品;王玉欣的《清泉一诺润山乡》字里行间,山泉既是具象的水源,亦是隐喻的精神原乡,作品最终升华为一曲对“美丽中国”的生动礼赞。
《长白文韵》的四重变奏呈现明显分野:小说重寓言性、散文强抒情性、诗歌求意象性、报告文学显政论性,形成多重、多维叙事模式。其深层价值,在于它用文学的方式回答了普鲁斯特之问:“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景观,而在于获得新眼光。”当生态文学不再只是环保宣言,而成为审美本体时,这些作品便获得了超越地域的普世价值——它们既是吉林的生态备忘录,也是人类重新定义自身在自然界位置的哲学草案,为我们留存了一本值得珍藏的生态中国精神图谱。(作者:杜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