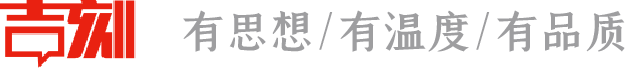在当代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版图中,王怀宇始终以其独特的叙事姿态开辟着属于自己的文学疆域。其发表在《中国作家》2025年第10期上的中篇小说《霍林河往事》,让这位“吉林西部文学现象”的歌者将其三十年的草原叙事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霍林河往事》既是一篇用文字编织的草原故事,也是一曲在时光深处回荡的心灵牧歌;既是游牧文明的精神显影,也是当代生活的棱镜折射。
首先,对于作家的创作而言,《霍林河往事》具有自我传承和赓续的意义。这篇小说延续了作者之前的长篇小说《红草原》(又名《血色草原》)对东北地域文化的深度开掘,却在叙事美学上实现了更为决绝的突围——当多数作家仍在消费“东北文艺复兴”的符号红利时,王怀宇已用黄榆木般坚硬的笔触,凿开了被冰雪覆盖的深层记忆。《霍林河往事》与《红草原》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契合度,都是书写草原上的家族往事,却又有着“全方位”的不同——包括情节设定、故事走向、人物塑造、人物性格、人物命运、叙事结构以及整体风格和写作手法等,这些都体现了王怀宇对写作更高的追求和全新的突破。
小说从1959年黑鱼滩“打狼队队长”选拔竞争切入,迅速把故事推向高潮,简洁直观地“领”出人物、“进”入矛盾、“掀”开历史,推动情节。使得小说叙事节奏自然流畅、巧妙紧凑。
在对人物刻画方面,作者没有运用过多笔墨,而是抓住比赛当日主人公家中每个成员的不同形态,展现人物性格,表现出作家成熟深厚的写作功力。比如:面临即将开始的比赛,一向脾气强硬的祖父忽然流露出内心的柔软、一向斯文的父亲突然中邪一样暴躁起来、逆来顺受的母亲因为不敢触了祖父的霉头强忍眼泪等细节,虽然着墨都不多,却极为精准地呈现出每个家庭成员此时此刻复杂的内心。对于祖父杨福堂,这场竞争是其渴望已久的、唯一能以公平的方式与冤家对头一决高下、一雪前耻的机会,却清楚自己的儿子并没有获胜的把握,从而既亢奋又忐忑;对于并不尚武的父亲杨临轩,则是尽管不情不愿却又不得不为家族的荣光而上场的暴躁;姑姑杨喜凤面对兄长和恋人之间的较量更是左右为难。她既不想看到哥哥惨败,又不想让恋人武元输了比赛——她和武元早已私定终身。每个人都各怀心事,于是每个人都立体生动、真实饱满。再如,仅写母亲对姑姑说的一句话,来表现母亲心理同样矛盾又复杂的写法,显现出作者在人物刻画方面的独到。“喜凤,你肯定盼着武元赢吧?”这句下意识的问话有几分尖刻的意味,但也正因如此,母亲这个人物立马“活”了起来。对人物的塑造非常接地气、生动鲜活细腻精准、体现人性的多面和复杂,是《霍林河往事》的一大特色。

二
摒弃传奇性、书写现实性是《霍林河往事》另一个重要特点。这是一篇经得起细细推敲的现实主义作品,选择的时间节点与所有细节都非常严谨、耐人寻味。 比如:五十年代草原孩子难得一见的糖块儿、入社时马匹悉数上交生产队、比赛前“借”回原先是自家的“战马”、比赛时出现的干部、比赛场零星的彩旗和掉漆的大鼓等等细节无不带着那个时代真实的印记。以父亲杨临轩这个人物为例,他对文学的热爱,最初来自一位“穿着板板正正的中山装”和“左面上衣兜里别着一支自来水钢笔”的下乡干部。 作者在这里将钢笔的金属光泽与中山装的棉麻质感形成的视觉符号,构成了杨临轩对文学最初的崇高想象,非常符合那个时代人们对新鲜生活的渴望。之后才有了他为了有机会读书写作,去当生产队的义务读报员,在报纸的空白缝隙里练习写文章。这与祖父杨福堂的期望相违背,也与草原世代尚武的习俗格格不入。然而正是读书让父亲杨临轩预见到新时代必将取代旧时代、新事物必将更迭旧事物,他那令祖父杨福堂愤怒、被霍林河人嘲笑的书呆子气,实则是终将覆盖整个霍林河流域的“全新命运”的先行者之孤独。这个人物的彷徨、踯躅,即是新旧更替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排异现象,他在比赛场上最终落败终究无法抵挡草原尚武时代的落幕——1959年的比赛成为日落前最后一道“霞光”,永远留在了历史的底页中。作为一个夹杂在新旧时代更替中的人,杨临轩性格中注定有着深层的矛盾乃至撕裂。他拂逆父亲杨福堂让他习武的指令,一意孤行热爱文学,骨子里却又秉承传统孝道;他不接受、不喜欢杨福堂的武断强硬,却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儿子杨昱正;他对妹妹喜凤和武元的婚姻横加干涉,却是妹妹殉情后最痛苦最愧疚的那个人。
祖父杨福堂同样是来自现实、诞生于“时代”的独特人物。他出生在旧社会,古老的尚武习俗深植他在的每根神经、每个细胞。他会做弓箭,会做打狼用的“掏捞棒子”,唯独不会弄虚作假。打狼队最鼎盛的时代,他距“拔得头筹”曾经仅一步之遥,可是武元的父亲武肇庆却用“阴招”大获全胜——不仅赢了他,还夺走他一条腿和他深爱的女人苏山丹。他对武肇庆的怨恨已不是简单的胜负所致,那是对品行和人格的愤怒、不齿,武肇庆的不光明不磊落,不仅表现在比赛中,也表现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他抢走苏山丹只是一种霸占,他的吝啬意味着他对这个女人没有真爱。苏山丹的投河自尽是一个女人个体生命的悲剧,也是男权社会的巨大黑洞。男人们自诩为能够战胜野兽保卫家园的英雄,对待女人的自私薄情,却又让“英雄”二字在草原的天幕下摇晃、蒙羞。
1959年的赛事结束后,一些人物的命运悲剧走到了终点,诸如祖父辈分的杨福堂、武肇庆,而另外一些人物的坎坷命运却刚刚开始。比如当上队长的武元和年仅八岁的杨昱正。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说在这里再度波澜暗涌,进入了下半部分的“出乎意料”和“不胜唏嘘”。
比赛结束时,父亲杨临轩重复了祖父杨福堂当年的败绩——失去一条腿。杨临轩被抬去城里救治之际,身为父亲的杨福堂和儿子杨临轩第一次各自说出真实的心里话。杨临轩对父亲道过,说自己“技不如人”,杨福堂却说是自己没忍住眼泪,“触了霉头”。这是他们父子第一次不再互相责怨、第一次把理解和体谅说给对方,没想到竟是最后一次。杨福堂当晚说出武肇庆当年使阴招的秘密后,撒手人寰。父子俩的和解和突如其来的分别是那么的陡然,令人不胜唏嘘。
杨福堂抱憾离世,加重了杨、武两家的宿怨。次年,以调教杨昱正骑马为契机的武元再次登门求亲,却被杨临轩连人带物“驱之门外”。杨喜凤也当着众人违心说出“你走吧,别再来了”的绝情话,致使武元伤心失落,在霍林河潜水时被巨型狗鱼咬伤,死于意外。杨喜凤悲痛不已,直接“跑”进了霍林河。老喇嘛为她超度时“吟诵经文的黑褐色嘴巴止不住颤抖,连同声音也像坐上了颠簸的马背”,人们发现诵经人颤抖的嘴唇里,藏着个比狗鱼牙齿更尖锐的秘密:喜凤的衣襟下,新生命正与霍林河的冰凌一同生长。一代人的悲情在另一代人的身上再度重现。
小说中对羊倌罗二的塑造也是一大亮点。霍林河畔最矮小的羊倌罗二,无论平时还是比赛时都是众人取笑的对象,唯独杨福堂说过一句认可他的话,也唯独喜凤曾经救过他一命。一心报恩的罗二为给喜凤报仇,蹲守霍林河五个昼夜,终于等来了罪魁巨型狗鱼,并最终与狗鱼同归于尽的悲情与壮烈延伸了文本的情感支脉。
在小说的结尾,一生嘴硬、且已因白内障失去视力的杨临轩,听到已成作家的儿子杨昱正纠正“巨型狗鱼其实并非狗鱼,是如今已经绝迹的一种黑鱼”时,大发雷霆,暴怒过后却老泪纵横,说出了埋藏心底数十年的话:“那是咱老杨家的老家啊……你太爷爷埋在那儿,你爷爷奶奶都埋在那儿……喜凤……你姑姑,她多疼你……她也埋在那儿……还有秀秀,也病死在那儿……狗鱼……咬死了武元、咬死了罗二……他们死的那么惨……你怎么敢说没有巨型狗鱼……”杨临轩这份最真实、最深层的心理,涵盖了过去的岁月、时代的变迁,涵盖了生生死死恩恩怨怨,涵盖了释然、谅解,也涵盖了追悔和无尽的怀念,格外让人唏嘘。

三
《霍林河往事》中语言系统的建构也是作者的一个独到之处。王怀宇创造了一种混杂蒙语韵律的汉语变体:支“黄瓜架”形容摔跤姿势,“物竞天择”与“自得其乐”的并置形成语义对冲,“男儿要争胜,男儿当自强”的草原训诫则通过重复吟诵获得咒语般的魔力。最具破坏性的是对暴力词汇的诗化处理:武元驯马时“用拳头砸裂鱼头”的想象,与杨福堂回忆折腿时“腿骨把心脏扎穿”的通感,共同编织成语言的荆棘丛。这种表达既不同于阿来《尘埃落定》的寓言式轻盈,也有别于郑执《生吞》的东北朋克美学,而是独创出“草原哥特”风格——就像霍林河冬捕时冰窟窿里涌动的黑水,在阳光下闪烁诡异的光泽。
在时空处理上,作者采用时间之物的包浆技法。1959年的选拔赛作为主脉,不断被三十年前的败绩、未来的作家身份等记忆碎片刺穿。这种时空叠印产生的蒙太奇效应,使霍林河同时承载祖辈的血、父辈的泪和子辈的墨汁。当老年的杨昱正用虚构为家族“改写历史”时,作家其实在追问:被掏捞棒子击碎的狼头骨与笔下复活的秀秀笑容,哪个更真实?早夭的秀秀,其“暖融融的目光”不仅终结了杨昱正的初恋,更象征着暴力美学传承的断裂。这种将女性作为文明尺度的写法,与白烨分析的“田小娥式祭品”不同,作者让女性在沉默中获得了比塔拉庙牌位更永恒的叙事权——当喜凤的羊皮护膝裹住杨临轩残腿时,草原上的权力结构已完成隐秘反转。
作者的生态意识早已融入在叙事褶皱里:被网住的麻雀“气性大得自己死在笼子里”,黑花马“像听到神秘咒语”般突然发狂,巨型狗鱼带着生态报复的寓言色彩。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象征手法,而是对草原法则的逆光显影。这种将自然力量人格化的处理,与李娟《冬牧场》的万物有灵论不同,作者笔下的草原生物始终保持着对人类的蔑视——当参赛者以为在征服自然时,其实只是在进行自然预设的残酷游戏。这种生态视角的革新性在于,它既非“天人合一”的浪漫想象,也不是环保主义的道德说教,而是揭示草原法则中永恒的吞噬关系。王怀宇将这种吞噬关系推演到极致:杨喜凤投河处泛起的水泡,既是生命消逝的印记,也是历史沉默的省略号。
《霍林河往事》写作手法纯熟,故事性、可读性强,通篇满具东北特色。打狼的独门兵器“掏捞棒子”,自制的“柘木弓箭”,射击比赛用的“老土炮”,光耀门楣的“狗鱼牙齿”,作者将民俗和老物件自然地融入情节,毫无雕琢,增加了小说的人文魅力,却全然没有“为了民俗而民俗”的狗皮膏药之感。这种化俗为艺的叙事策略,使文本既保持着冻土般的粗粝真实性,又具备驯鹿皮般柔韧的文学质感。
文本中作者作了大量赓续草原历史传统的草原知识性叙事,也正是因为围绕吉林西部叙事而生成的知识性叙事、文化性叙事,以及围绕文化与地域考古学意义表达所作的现实性书写,由此所形成的小说叙事才既接续了文化传统,又烛照了现实社会与现世人生。
除了文学地理叙事意义维度的探索,中篇小说《霍林河往事》也在现实题材与历史叙事融于一体方面,显示出作者具备较为强大的叙事调度的能力。在小说中能够看到王怀宇在苍穹与大地之间跋涉的初心,当杨昱正把家族败绩改写为文学胜利时,整个吉林西部草原都听见了文本反抗现实的马蹄声。这让人想起胡平先生对《繁花》的评价:“最好的地域文学恰恰是要消灭地域的”。王怀宇的野心或许更大——他不仅要让霍林河水倒流,还要让所有被命运击倒的杨福堂们,在文学镜像中重新挺直脊梁。当镜中人终于与祖父的身影重叠时,那个关于“草民就要像草一样顽强”的古老训诫,终于在叙事的春风中获得了重新翠绿的权利。(作者:杜波)
作家简介:王怀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作家》等刊发表作品六百余万字,曾获梁斌小说奖、田汉戏剧奖、冰心散文奖、长白山文艺奖等奖项。
作者简介:杜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白城市作家协会主席。其作品散见于《中国报道》《中国环境报》《中国文艺报》《诗刊》《中华读书报》等。有诗歌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朝鲜文、蒙文等。
图片:图虫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