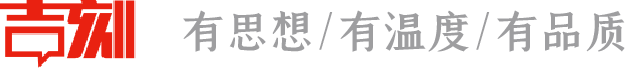道路是大地上的行走者。
在远古,这个行走者曾是人类踩踏出的“羊肠小道”,渐渐成为地表上“狭窄的纹路”。古老的纹路里,布满古人迁徙的足迹,也悠荡着象征人类最早商贸行为的“驼铃声声”。日升月落,大地上的行走者用“低头赶路”和“永不止歇”,织就了人类文明最初的脉络。《诗经·小雅·大东》里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描述,按照路面宽度和走向,这应是周人东迁之路, 堪称最早的国道。
“道路”自身就是一部悠久的变迁史。而国道,从“西周早中期古道”到“秦朝驰道”,直至当下“纵横穿梭、贯通四方”的二百条以G开头的“国道”,已在华夏大地行走三千余年。每条国道都有既清且明的方向,从不迷失。每个初始都通往一个遥远的终点,就像每个黎明都会降落在守候它的那个黄昏。至于沿途何处会有灵魂生成,或者有故事可以入“史”、入“文”、入“戏”,再不济,入眼、入心、入魂魄也是求之不得的事——就要看缘深缘浅、相看是否相宜了。
早冬,站在G334国道延边段龙井起点,对于这条道路即将带领我相遇的山河、江湖、民居、阔野、边境线、苍鹰、灰鸽子和有缘人,我是芸芸众生中一个慕名而来者,一个静默寡言的凡间客。
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百姓的朋友”,“是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天性难改的乐天派。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那是很长的一段描写,旨在呈现苏轼作为人的丰富和立体——他是什么人,取决于他置身何处、对面何人。G334作为大地上的行走者,它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同样取决于跟随它、打量它的眼睛——是停留在眼前,还是心意虔诚地回首,或张望。
眼前的它只是一条道路。蜿蜒在大地之上,平坦,起伏,“九曲十八弯”。遇上高山,它会变身隧道,遇上江河,它是凌波俯瞰的架桥。它悠长、坦荡、天真、一览无余,却又在你想驻足的每一处,备好清凉的山泉、精酿的米酒、滚烫的咖啡,邀你小坐,就着窗外有故事的大黄杨、揽照邻邦也揽照故里山河的黄月亮,和你共话一段淙淙过往。
透过枝头那缕青色的光,它如晨钟暮鼓般淡淡启齿——
我的朋友,你看北兴村朝鲜族百年老宅时,老宅也在看你。你捧起不老泉的泉水时,泉水会记住你的脸庞。它会托早冬的风吹动大黄杨尚未离枝的叶,告诉你这里是中朝边境三合村,这里的十一棵大黄杨已经八十岁,比任何一位戍边战士都年迈。它们秉承大自然的旨意扎根此处,日夕坚守,八风不动。它们见证岁月,也见证和平、安定和每一点细微的变化。比起它们,“古树咖啡屋”和里面制作咖啡的年轻人,是时光为它们带来的“远方的世界”、“摩登的城市”和“蓬勃的青春气息”,是新的探索与追寻。
与一条道路的交谈就这样开始了,自然而然。苍鹰正飞过路两旁的群山,山上无雪,不落叶的柞树远看像盛开着一团团老金色的牡丹。更远一些的山脊,此时长满细密的“汗毛”,那是些光秃的树木,细高、笔直、昂然的树木。落叶把每座山都染成了金色的山丘。某个瞬间,寒风啸傲,触景生情般想起李宗盛——歌声里越过的山丘,在人间这偌大戏台上,他真的越过了吗?
十一月初的图们江和海兰江尚未封冻,叮叮咚咚,在国道旁,唱着“冬来不在秋尽处”的欢歌。细听,那是无比熟悉的曲调,是历越六十载光阴却明媚依旧的旋律——“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 G334已经带我来到和龙市崇善镇元峰渠,歌曲《红太阳照边疆》的故里。儿时记忆里,我登台唱过这首歌,对于我,它意味着光洁的额头,洁白的年华。对于六十年前的延边人民,那是一段与天斗、与地斗的光辉岁月,是棱棱高山、狭长谷地,是横跨红旗河的上天村元峰倒虹吸。民以食为天,这是“千百年来民众生存活命的大真理”。有了水,六百米高的长白山东麓台地便成了百姓的“饭碗”。在历朝历代的百姓心中,粮食都是最有烟火味、最实在的福气。成熟饱满的稻穗会把笑容朝着美好富足的生活绽放出来,这多像我们的祖先自古就为丰年和安康,烹羊宰牛、会当痛饮、载歌载舞。
在和龙市光东村,属于这个时代的“新”与“欣”,与村史馆里习总书记的影像、收割后准备猫冬的稻田一道,扑面而来。总书记的关切、朝鲜族村民的笑语、广袤稻田的丰收气象,属于光东村,也属于整个延边大地。幸福,在这里是具象化的名词,也是一个金色的形容词。它集结着土地、人民、勤劳、信念、汗水,镌刻在每个人的眼角、眉梢,也轮回在这片大地年复一年的春耕秋收、廪仓廪实里。
G334以一条道路的耐心,陪我追忆这片土地的“似水年华”、“光辉过往”,然而它脚步不停。它不是时间,可它又像铺陈在大地上的、有了形状的时间。它将我送至某地,又静候我随它离开。对“时间”一说,它报以坦诚的微笑:我的朋友,时间不该像我一样平淡,乏善可陈。时间应该在药水洞、西古城那样有血性、有枯荣的地方,等待有缘人“倏忽而至”。
对于血性和枯荣,究竟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有缘人?晚霞正把天空缀满酡红,若隐若现的木鱼声在天幕低回。“谁此刻孤独,谁就将长久孤独。”里尔克道出了谁的心声?孤独者,还是那些“灵魂高不可攀”的得道者?
药水洞全称“药水洞苏维埃政权诞生地”,是一个与抗联、与东北最艰难岁月息息相关的“肃然之地”。1930年5月,这里发生过“红五月斗争”,1932年11月发生的“药水洞惨案”,金顺姬等八名革命志士葬身烈火。1937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师军需部长朴相活,为掩护战友撤离,只身诱敌,跳崖牺牲。
“山静似太古”,这是药水洞给我的第一印象。转眼就被历史的苍茫喧哗了。鲜血浸染过的地方,连风都是凌厉的,苍凉刺骨。唯一的告慰,当属朴相活烈士1931年亲手种下那棵柳树。作为百年老树,它粗放、健壮,站在紧贴它的角度仰视,它“达地通天”——能大声宣告的,与苍天共鸣;必须默默隐忍的,深藏地下。这一百年,它遭受过人的摧残,雷电风暴的摧残,没有倒下,反而糙实壮硕了。《淮南子》里有句话,“精者神之气,神者人之守”,一个“为义而殉者”把灵魂寄放给一棵树的累生累世,树便得到了托付,有了使命。而壮烈的灵魂,因为有了守卫,便会愈发贵重、获得恒久吧——由古到今,聚散轮回死生契阔,遇见有灵魂的人、有灵魂的树,哪怕匆忙交错中仅有一个对视、一个颔首,也值得铭记一生。
毕竟,时间太浩瀚,无数无常中的一个微末,便能让彼此错过。
没错过的,还有月光下的西古城。
作为渤海中京城遗址,这里曾是盛唐的“国中之国”。鼎盛时期的渤海国,“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史称“海东盛国”。大钦茂在位五十七年,享尽繁华与“帝王之威”。可以想见,向大唐进贡“太白之兔、率滨之马、卢城之稻、北海之鳍”的他,坐拥与长安城风格接近、由内城外城构成的双重城垣的他,曾是何等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一千二百年后,站在二号宫殿遗址旁,遥想唐廷对大钦茂的册封、汉字成为渤海国通用文字、盛唐的灿烂文化在渤海国开出繁花——不由感叹,寰宇间最强大的,莫过于时间之威。唯有时间,能见证所有荣枯,一棵树、一条河、一个城池、乃至一种人类文明。
当一条道路对你倾谈这一切,它便不再只是一条道路,而是一位沧桑老者、一个心有乾坤却满目慈祥的老友、一个饱经世事却波澜不惊的“大地上的行走者”。它笑纳一切,荣辱誉骂、寒沙凛冰,从不解释。在它灵魂深处,“道路”即“道”,是“朝闻道”的道,是“道法自然”的道,是“一朝得道”的道。这深刻的认知让它坦荡安宁,从不惧怕风雨雷电的袭扰,不惧流言、是非、歪曲和跳梁小丑的表演。它信仰“人间正道是沧桑”,它深知,永远有人如它一般古朴、守拙、追寻恒久的真理,他们需要和它一样如如不动、静默安稳的“心灵大道”。
在G334沿途,我是一个心怀感激的人,一个不奢望被记住、却被这条路上的某地、某物、某人悄然打动的人。作为大地上的行走者和人类步履的承载者,G334拥有古朴的底蕴和原汁原味的北方风情,自成一格。它是道路,是注定的远行者,又何尝不是一部行走的自然史、民间史、风物史,一部弥漫烟火与温情的生活史呢。(作者:杨逸)
图片:图虫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