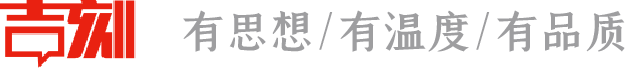在延边,老白山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它矗立在吉林省敦化市黄泥河林业局团北林场附近的群山之中,平日云雾缭绕,云蒸霞蔚,一片云海。从远处看去,就像戴着一面白色的头巾。莽莽苍苍的群山属于长白山脉张广才岭,因山顶积雪时间长,故而被称为老白山。这里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湿地类型独特,植被垂直带显著,被誉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老白山的雪线之上,总有几簇墨绿在云影里浮沉。那是偃松,把根扎进岩缝里的“树中隐士”,用蜷曲的枝丫,在海拔两千米的高岭,画出一幅永不褪色的山水。
初见时只觉奇怪,这般天地,风如刀,雪似刃,连岩石都被啃噬得棱角尽失,偏这矮松倔强地活着。它们不似山下的松树挺拔如塔,却自有一番筋骨:主干贴地匍匐,枝丫向四方伸展,像一群俯下身的武者,以谦卑之姿对抗着高寒。树皮皴裂如古陶,沟壑里藏着数十年的风雪,每一道纹路都是与时光博弈的勋章。
离远看,这几株偃松就像几片硕大的苔藓贴在地上。这些偃松绝不孤长,它们密密匝匝地挨在一起,并互相挽着手臂,像伏卧的士兵。高山偃松个头不高,最高的也不到两米。它们根部粗壮,或虬曲嶙峋,或旁逸斜出,如同放大的盆景。
偃松的叶子与其他松树区别不大,一根根松针纤长挺直,密密地长在松枝上,能遮挡阳光,留住一地阴凉。由于枝叶密不透风,长势又矮,所以偃松的下面像是一间间窝棚。偃松的绿与其他松树的绿是一样的,绿油油的,这种绿很稳重,也很苍老,像压缩后的绿色。不管寒来暑往,还是斗转星移,偃松始终是一成不变的颜色,颜色里有时光的厚重、古朴和沧桑。面对高海拔、风大、寒冷的气候,只有逐步适应恶劣环境,才能生存下来。这就是生存劣汰、适者生存的道理。它把根扎在深处,或者在岩石的缝隙间,在千百年的演化进程中,把自己的身体变矮,以此来对抗强风。面对严寒,它把自己蜷缩起来,减少受寒的面积。当你看到或想到这些时,你会感叹它生命的顽强。它有极强的适应性,生态系统能随环境而改变。它还是老白山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系可以固定土壤,防止水土流失,为众多高山动植物提供栖息地和食物来源,维护着高山生态系统的平衡。
偃松也有松塔,但松塔相对较小,呈卵圆形,如鸭蛋般大小,外皮软,成熟时为淡紫褐色或红褐色,香味浓郁,有风吹来,香飘十里。每当云雾升起,在老白山的半山处飘荡,这时的偃松林就像是天上的饰物,云海在偃松的脚下翻滚,仙气弥漫,而那些匍匐的偃松就成了天空中最醒目的风景。
春日融雪时,松针上凝着的冰晶簌簌坠落,砸在石面上叮咚作响,恍若偃松的私语。最动人的是它们的姿态:有的单株立在崖边,枝丫朝着风来的方向倾斜,像一尊凝固的雕塑,守着亘古的孤独;有的三五株抱团而长,根须在地下紧紧相握,枝叶交错成伞,替彼此挡住最漂冽的寒流。盛夏时,松针间会冒出淡紫色的小花,细碎如星,在云海翻涌的背景里,竟添了几分温柔。那时才懂,所谓坚韧,从来不是生硬的对抗,而是在残酷里长出柔软的希望。
山风掠过,松涛声细得像耳语。这些长在云端的树,早把日子过成了哲学。它们懂得低头——低于流云,低于飞鸟,却高于所有妄自尊大的脆弱;它们懂得取舍——放弃向上生长的高度,却把根系扎进更深的岩层,用横向的扩张,在贫瘠里拓出生存的疆域。当暴雪压弯枝丫,它们便轻轻抖落积雪,不与天争强,却在妥协中守住了生命的尊严。这让我想起古人说的“大丈夫能屈能伸”,原来天地间的智慧,早被一株矮松参透。
暮色漫上来时,偃松的影子在石面上拉得很长。它们是老白山的标点,把荒芜的山巅连成诗行;是时光的证人,看尽了千年的阴睛圆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的姿态。当城市里的人在钢筋森林里迷失方向,或许该来看看这些树——在极致的孤独里扎根,在无常的风雨里安身,于卑微处见风骨,于寂静中见辽阔。
山风又起,某片松针上的露珠滚落,摔碎在岩石上,却在阳光里折射出彩虹。这便是偃松,不是屈服,是与世界达成和解的温柔力量;卑微不是渺小,是扎根土地的厚重。当我们学会像偃松那样,把根系深植于生活的岩层,哪怕长不成参天大树,也能在属于自己的高度,听见风穿过枝叶的清响,看见云卷云舒的自在。
老白山的夜静下来了,偃松在月光里轻轻摇晃枝丫,像在与星辰对话。而我忽然懂得,所谓生命的深度,从来不在高度,而在与土地相拥的温度,在与风雨共舞的从容。就像这些长在山巅的偃松,用一生的蜷曲,写成了天地间最苍劲的诗行——关于坚韧,关于谦卑,关于在荒芜里种出自己的春天。(本文节选自《云海之上》)
作者:杨树
来源:《长白文韵》
图片:图虫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