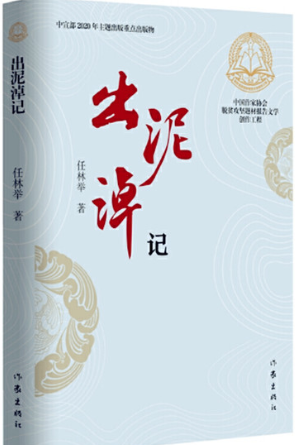
对话嘉宾:
任林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近年主要从事报告文学、散文及文学评论的创作。著有《玉米大地》《粮道》《时间的形态》等。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老舍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三毛散文奖等。2020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出泥淖记》。
任白,1962年生,作家、诗人、媒体人,发表诗歌、小说近百万字,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失语》、诗集《耳语》等。
任白:林举好,首先祝贺《出泥淖记》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得以正式出版,在我的印象里,和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这部《出泥淖记》显得更为坚实,从文本中留下的那些刀砍斧斫的痕迹也很容易感受到写作过程的不易,能说说全书脱稿那一刻的感受吗?
任林举:谢谢,也谢谢你的认真阅读和理解。无论从采访过程还是写作过程,这确实是进行得比较艰难的一部作品。
先说写作的定位与构思。脱贫攻坚以来,文学界和社会各界一样,对这个“国家行动”异常重视,针对脱贫攻坚的写作一时蜂拥而起,粗算下来,这一两年间写脱贫攻坚的作品也不下千部。集中力量反映时代主题和重大事件,当然是好事,只是在争先恐后的表现热潮中,写作者的情绪和视角都容易被裹挟、同化,发生“集肤效应”。大家都把精力、热情、思考、笔触集中在最容易摸得着、看得见、好表现的事物表象,谁也不往深处想。然而,文学不同于新闻报道,不同于经验材料和事迹报告,它需要作家避轻承重,放弃谁都看得见的捷径,走远路,走难路,走看似无路的路,也就是自己的路。虽然基础材料在性质上可能相似或相同,但在构思和总体立意上必须要突破“众口一词”和“千人一曲”的重围,否则,作为文学就失去了存在价值。
再说采访。当一部作品的结构和立意确定之后,它重点关注领域也就确定了。当别人都把目光锁定于“大国”“大省”“大县”或“重器”“重镇”的时候,我主动选择了避让,走到边远的乡下或山村,在边缘或边缘的边缘寻找、开掘自己的矿脉。考虑到这场脱贫攻坚最终的落脚点就是中国的广大农村,我只能避开单一的“网红村”或“明星村”,采访更多的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村庄。如此一来,路就更远,更绕,更加难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了吉林省具有代表性的广大农村,平原的、山区的、旱作区的、稻作区的、干旱区的、雨水丰沛地区的……时值寒冬,东北大地的道路上积满了冰雪,一下高速公路,走的都是狭窄、弯曲的乡间或山间小路,危险和艰苦如影随形,但我确实没有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我自信自己比它们走得快。
当这一部作品终于出手时,我感觉像爬了一段坡路之后的小憩,也还是有一点儿小愉悦的,毕竟我以自己的方式已经完成主题的表达,同时,在作家和作品上,也向着真正的完成又努力迈进了一步。
任白:看到《出泥淖记》这个名字时,我直觉到其中隐藏的野心,记得当时我和你说想起了《出梁庄记》,但你脱口而出的却是《出埃及记》,你的野心比我想象的还大。《出埃及记》当然是一部史诗,《出梁庄记》也有内在的史诗品格,都是一个族群力图摆脱巨大困境,实现战略转移(型)的惊心动魄的艰苦过程,这是一种隐形的史诗结构,有一种内在的宏大。我不太同意有评论说这部作品亮点在于细节的说法,细节当然也很出彩,但这种结构所带来的意义空间显然更具决定性,这是你的初心吗?
任林举:你说得对。我一直觉得文学是关于无限大和无限小的艺术,或者说,是无限大和无限小之间相互转化的艺术。当我们的笔探微至无限小时,小到基因或原子,甚至更加微小的粒子和波,所有的个体都消失了,但它的本质在这里得到了放大,每一个基因和粒子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个体,而是群体、整个物质世界或宇宙的信息。反之,当一种事物被无限放大它便化作虚空或虚无,便没有谁有能力感知到它的存在。我们都知道文学必须解决好个体性和总体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却经常忘记在作品中自觉运用和解决。很多纪实类作品,经常缺少的并不是故事,而是两种必不可少的文学元素,一个是细节;一个是隐喻。细节把事物的小放大成大;而隐喻则把庸常的事物安置于无限深远的时空,成为诗性的存在。
在《出泥淖记》中,我重点考虑了如何弥补纪实文学通常所缺少的元素。生动的故事和细节已经被一些人看到了,也说到了,但整部作品以及具体故事的隐喻性和象征性却被很多人忽略了。之所以被忽略,大概是因为一般性的阅读,并没有注意故事与故事、故事与主旨、人物与人物、个人命运和整体事件以及社会运行轨迹之间的关联,更没有把一个国家的脱贫攻坚和中国历史以及人类历史关联起来。我觉得,这么一个史无前例的脱贫行动,它已经具有了史诗性,它将永久地改变一些人的命运和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
抛开宗教不谈,我们只谈历史。想当初,摩西为了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是一件多么惊天动地,又是多么艰苦卓绝的事情。从埃及到约旦河西岸远不远?不远,但那却是一段多么艰难、曲折、反复迂回、阻力重重的一段路啊!一走就是40年。那么,这段历史上最著名的路程,它的难,难在哪里?直接地说,就是难在人心!难在人们的蒙昧、无知、贪婪、犹豫、抱怨、怀疑、没有信心和难以统御。抚今追昔,反观我们的脱贫攻坚,其难点说到本质也不在资金、项目和物质。物质作为基础当然有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但最重要的还是人心,是人的意识、观念和自觉行为。当人们身处困境或在挣脱困境的过程中,决定最后成败的,就是人性。如果说野心,我也许有那么一点点,一开始我就想把《出泥淖记》这部作品写成一部白话史诗。至于是否能够做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论能力和条件是否具备,理想总是要有的。所以在写这部作品时,我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扶贫的过程和结果上,而是放在或黑暗或光明或兼而有之的人性复杂性上以及由人性的复杂性给脱贫攻坚造成的巨大难度;进而将单纯的故事演化成人物命运的起伏和变化。总之,我在写《出泥淖记》时始终没有忘记一点,就是尝试通过具体的人物和故事,为脱贫攻坚这个重大事件在时间或历史流程里上找到一个不会被磨灭的点。
任白:难在人心,这一点我完全同意。怎么想到“泥淖”这个词的?作为一个统摄全书的意象,它主要传达的是农村现实的复杂性?农业文明中很多负面因子作为一种传统的“不可断绝”?还是从产业角度讲,现代化本身就是一次新的长征?
任林举:贫困,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有时并不是用有钱或没钱来定义的。有些人陷入贫困之后,总要前方百计地往外挣扎、突围,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能走上富裕之路。而对于有些人来说,一旦进入贫困状态后,精神和意志都随之跨了下来,不再挣扎,也不再有挣扎的力量和勇气。因为挣扎就意味着投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投入。有一些运气好或善抓机遇的人,投入了就会有效果,使自己的状态得到了改善或根本好转,但多数人因为缺少斗志或能力较差,只能在贫困中越陷越深。
想一想这件事儿、这种现象,自然中有什么和它相似呢?
我小时候家住平原,不远处就是一片湿地。湿地上有一种东西叫“泥淖”,俗称“大酱缸”,这和新华字典里的词条解释“泥坑”有极大的不同。泥坑有深有浅,而我们说的泥淖似乎是深不见底的。一个人、一匹马掉进去,挣扎一会就被吞没了;一挂四套马车陷进去,挣扎一会儿也被吞没了,并且进入泥淖的生命不能挣扎,不挣扎会慢慢下沉,等待着外部的求援来到,就可以从外部将其救出;如果不懂其秉性,拼命挣扎,会越挣扎陷入越快,不等救援到来,早已演变成灭顶之灾。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地理现象,它像一道布设于大地上的魔咒,对陷入其间的生命,有着神秘而不可挣脱的吸附、吞没力量。是的,人类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一直和贫困做着不懈的斗争。想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中,一直不能彻底摆脱的贫困,不正如一个无影无形却无处不在、司空见惯却又难以设防的 “大酱缸”嘛!一旦我们把泥淖和贫困这两个意象联结到一起的时候,一个广阔而深邃的叙事时空,立即在我的眼前打开了。
这个泥淖,表面上似乎是自然条件、资源、资金等物质因素造成的,所以有人认为这些深陷贫困的人,有了“来钱的道儿”就能摆脱贫困过上富裕日子,可实际上,并非如此。现实告诉我们,即便有人通过外力获得财富或温饱,也还会有人因为过度消耗和管理不善、损毁等原因而变得一无所有,也有人因为意外的变故而使手中的财富散失殆尽。人性的种种应力,社会的种种争竞、命运的种种颠簸,竟然是贫富差距的最大动因。特别是当物质上的条件和机遇几乎均等时,人的心性、观念、思维、行为习惯等精神因素便显得尤其重要。
你以“新的长征”做表述,我认为是准确的。如果说,减贫或脱贫就是横跨人类生存史的一场旷日持久的长征,那么在这个“长征”中,我们可以消灭绝对贫困,却并不能消灭相对贫困,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站在新的起点上,开始新的长征。
任白:全书对脱贫攻坚艰巨性的深入书写令人印象深刻,很多章节充分展示了令扶贫干部措手不及的一些乡村现实。比如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对基层权力无孔不入的渗透,比如贫困农民的颟顸与惰性,等等。有些细节既令人忍俊不禁,又让人难以释怀:大安市大岗子镇整体搬迁,贫困户们诸多不适,有的想起简陋但却“温馨”的老屋,嚷嚷着要搬回去;单身老人李秋山在新居里更是无所适从,甚至上厕所都成了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在采集和记录这些细节时,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任林举:人性以及有人性交错而形成的现实,总是出乎意料的复杂,有时甚至不可理喻。除了你点到的一些现象,还有更多复杂的社会现象。有的村级干部认为扶贫工作队的进入是对他们原有特权的一种剥夺,消极抵抗;有的认为有工作队在推进工作,自己就可以啥也不管了,坐享其成;有的利用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工作队周旋,只要利益不要出力。就是贫困户本身对扶贫工作的认识和态度也各不相同,有的贫困户认为扶贫不是他们自己的需要,是国家的需要;有的甚至认为原来的日子过得很好,被别人逼着干这儿干那儿,是被打扰;有的认为扶贫就是临时的一项困难补助;有的人还赖在半地下的土房里坚决不出来……正所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标准和应对方式;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是非观。
无疑,这些复杂的人性和千差万别的观念和理念给脱贫攻坚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工作难度。我之所以要在作品中呈现人性的复杂性,主要还是想告诉人们,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人也好,真想办成一件好事难度都是巨大的。也正是有这么巨大的难度,才反衬出广大扶贫干部的巨大付出,也才显现出脱贫攻坚的含金量、意义和价值。
任白:你写了一批了不起的扶贫干部,有奋力破除五人沟村权力网,立志更新村民脑子里的“软件”的老孙;有从带头扫大街开始理顺著名上访村民意的王平堂;有为配齐配强村级领导班子殚精竭智的乡长田金鑫;有让无望者重燃希望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李鸿君;有“延边州朝鲜族的焦裕禄”韩哲忠,等等。在你看来,这些带领村民筚路蓝缕,走出泥淖的带头人身上有什么共同的特质?是什么让他们在重重困难面前选择坚持和担当?他们在脱贫攻坚这个阶段性使命完成后,给中国的乡村建设留下了哪些重要的遗产?
任林举:我认为,他们身上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从个性的角度说,都有着英雄主义倾向。英雄是人类史上最稀缺的资源,但英雄如烈酒,也提气、提神,也辛辣、霸气。如果继续探究更深层次的动因,用公共话语体系阐释,就是他们骨子都有着“利他”情结或都有高尚的情怀。
这部分人除了情怀之外,还有常人并不具备的天赋,就是不但有公心、公义,还有较强的能力和方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领导素养和领导才能。这些人在农村工作一段时间就已经把先进的观念和文化以及先进的管理方法带到了农村,也对所在村庄产生较大的影响。于村民来说,看到了好干部应该如何做事,对于一些知识、观念、能力有限的村干部来说,学到了先进的文化、理念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但对另外一些村庄而言,如果没有好的带头人和合格的传承者,并不能将这些典型人物带来的先进文化、观念和管理方法保持和发扬光大,就很难说都能把他们的精神财富作为一种“遗产”留存下来。
任白:你写了一个成功的农民李雅繁,这个后来成长为公司董事长和“吉林好人”的乡村女性有着回想起来“令人心悸”的奋斗历程,她和丈夫身上的很多特质,比如无论如何也要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奋斗精神,从不小富即安的心胸和眼界,等等,好像更像我们熟悉的南方企业家。用五人沟村第一书记老孙的话说,他们脑袋里的“软件”应该是升级版的,这是天生的吗?他们自身的现代化有外力相助吗?他们成功的关键是什么?他们的成功对于吉林的高质量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有什么启示和示范意义?像李雅繁这样成功的现代农民企业家在未来吉林省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还能发挥什么作用?他们会不会像一颗在我们吉林的黑土地上培育出来的优良种子,造福更为广大的乡村?
任林举:像李雅繁这样的人,虽然并不是天生就有一个“升级版的头脑”,但也绝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这样的成功者,不但要有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品格,还要有不同于普通农民的眼界、观念和意识,甚至境界和胸怀。这不是别的问题,是文化,是观念,是意识。北方城乡的观念和意识比较南方相差甚远,城市与城市比较要差至少10年,农村与农村比较至少差20年。早在30年之前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农民们就已经“家家做买卖,人人当老板”了,至今已经有数百个国际知名、国内前排的巨型企业集团和知名品牌,而吉林省目前还很难找到那样的企业。李雅繁之所以有这样的意识,主要原因之一,是得益于她的家族传统,从小就有摆脱贫困的强烈意识;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从商的原因,很早接触了南方经商同道,较早地和发达、先进地区在文化、观念上实现了接轨。她是碱土地上碱蓬丛中一棵拔了尖儿的红高粱。
这样的人,肯定会在未来的奔小康道路上成为一个新型的农民典范,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效仿和学习的榜样,我坚信随着文化土壤的日益改善,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李雅繁在吉林这块热土上成长起来。
任白:脱贫攻坚触发了中国农村一场深刻的变革,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推动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使广大乡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人口结构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比如在韩哲忠的运筹之下,为数不少的赴韩打工者回流榆树川就是典型的案例,这种变化是刚刚开始吗?第六章结尾,当有人问吴其新:“扶贫验收完,扶贫干部就要走了,你咋办”时,吴其新沉吟半晌回答,“咋办?靠自己呗!”这个似乎是被逼出来的答案,是不是可以视为一大批原来困守贫困的农民正在觉醒?
任林举:人口的迁徙和流动,总是避害趋利的。哪里有财富,哪里好过活,人就自然向哪里流动。中国的农村人口之所以会大量流失,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农民们所拥有的资源维持不了他们想要的生活。随着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以及脱贫工作的深入开展,一些出走的农民或子弟如金君等,在自己离弃的土地上看到了新的商机和新的希望,自然会顺理成章地回归。能在自己的故土过上美好富裕的日子,谁愿意背井离乡呢?应该说这种回归是动态的,随时都会发生,但比较密集的出现,还是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农村扶贫政策和新农村建设力度加大,变得美丽、美好的乡村渐渐显现出巨大的魅力。
就我个人理解,全国性脱贫攻坚主要任务是给绝对贫困人口在物质上提供一个起步的机会,精神上来一次“软件升级”,提供一个未来问题的解决方案。“扶上马送一程”之后,好日子还要靠自己去“过”,去不懈努力。人类社会是一个群体性社会,任何一个概念都要放在更大的范围和体系中去考量,所谓的公平、合理也是这样,从长远和全局的角度说,对少数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人终身包保,便是对大多数勤劳持家农民最大的不公。脱贫攻坚的出发点也是这样,其工作定位也始终把重点放在了“扶志”和“扶智”上。经过这场洗礼之后很多农村贫困人口都醒悟过来了,所以吴其新才说“咋办?靠自己呗!”他是“脱贫后”时代的一个代表,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
任白:在《出泥淖记》之前,你还写过《玉米大地》《粮道》等农业农村相关题材的优秀作品,应该说,你对吉林省的农业农村发展现实非常熟悉,按照你的理解,在未来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学应该以什么角色参与其中?
任林举: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中国乡村的变化才是中国社会的根本变化,它牵涉到国运和每一人的命运。所以这个领域也是文学必须关注的领域,像关注我们时代一样关注乡村振兴。当然,文学有文学的角度,我们不能像行政机构一样,参与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但我们要在全过程中关注人们内心和精神世界的变化,也许,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历程。
任白:你是个有很强的文体意识的作家,每个章节前,你都写了一段箴言式的诗句,比如“——不要不敢相信\河水会为你分开\你的路本不在大地上\而在岁月深处”,这种与正文内容迥异其趣的文字一般读者初看会觉得有点生涩,这么写的意图是什么?
任林举:说到文体,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虽然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的特征和框范,但每一种文体都不应该画地为牢。实际上,很多优秀文本都尽可能多地吸收了其它文体和其它艺术门类的营养,借鉴了其它门类的艺术表达手法。特别是纪实类文体,从来就没有现成的理论框架,最准确的表述也就是关注和反映现实的文学。既然是文学,就不再有表达方式的限制。我一直认为纪实文学的优势正在于它比其他文体具有更大的艺术伸展空间和表达自由。它可以使用新闻语言体系,也可以使用小说语言体系,也可以使用散文语言体系,甚至诗性的语言和结构,为什么要死死抓住新闻语言和手法不放呢?没有人规定报告文学就是报告而不是文学呀!报告只是针对一个基本事实、表现,最后还是要遵循和回归于文学。
我说过《出泥淖记》一开始设计的就是一个史诗的框架,但由于故事离我们太近,每一人都不愿意赋予其足够的隐喻和象征意义。也就是说,这些眼前的、日常的材料要想让人们重视起来,往深处想、往远处想,玩味故事背后的深意,必须要找到一缕光将它们照亮。那么每一章之前的诗句箴言,就是照亮全章故事的光,它是一章的主旨也是时间上的坐标。有了它,阅读者才有可能把这些现实材料放在时间深处去打量;有了它,这一章的故事才与另一章的故事有了逻辑上的关联;有了它,这一章的故事才能与总题目有了紧密的链接和呼应。如果把总题比作屋脊,这些诗句箴言就是梁柱,它们共同联结、照应、支撑,构筑起一个诗性的结构。
来源:吉林省作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