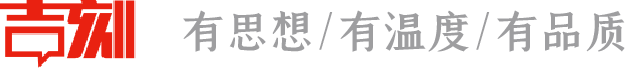春天也是登山者
春天的攀爬也是从山脚开始的
那些从冻伤中起身的芽孢
像破冰一样蜕掉褐色的硬痂
钻出头顶的雪线
开始向着山顶
迈出轰然作响的脚步
那是季节穿越疲惫的轮回
再一次推开生命之门的脚步
那是草木掀掉身上的万千残骸
再一次把生灵注入躯体的脚步
那是牛皮杜鹃想去更高处
举起鹅黄色喇叭的脚步
那是历史强制自己忘记每次湮灭
用残损的手指翻开新页的脚步
那是羲和和夸父的脚步
是汉尼拔和亚历山大的脚步
是尤利西斯十年返乡的脚步
是斯科特和阿蒙森的脚步
是雪线在春天的托举下
一点一点上升的脚步
我还是更爱北方的春天
我还是更爱北方的春天
无数绿色的舌尖
从衰草的遗骸下钻出来
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
它们有九万条命
它们有九万条命
尖细的啸叫渐渐宏大
在地表之上结成电磁围幔
一条绿荧荧的飘带
抱着我们复活时
雷电的荆冠
我对明天的全部信念
都是北方春天规劝的结果
是青草、野蒿和漫山梨花
一同告诉我的
还有丁香树
它的甜蜜里还闪着旧疾的光芒
干裂的土地也被春水弥合了
江河在大地上流淌
今天像昨天和明天一样
春夜
又逢春夜
前两天下过一场雪
但早就化掉了
对面的单元楼是灰黑色的
有些窗口亮着灯
我查了查,一共19个窗口
那里面一定有老人、孩子
一定有胃口不好的中年男女
正在劝孩子们
吞下对明天模糊不清的承诺
有谁会留意
楼下洋槐的枝条
再次变成春天的毛细血管
而这个无名的夜晚
又局部又孤单
无法成为我们欢呼的理由
无法让我们忠实于每个春天
无法承诺我们都会
应约变得饱满而又蓬勃
但无论如何
草木枝干里的径流
让人想起前世的歌声
一个晴天
我坐在小区的花园里
茉莉举着星星
垂柳抖动裙摆
从湖面上吹来的风
轻轻掀动我的衣襟
我感到愉快
感到世界正以一种
友善的方式运作
这有多么好
阴影不会带来怀疑
愚蠢不会膨化慌乱
这有多么好
我坐在一个晴天里
夜晚缩在墙角
记忆赐我谦卑
有一天
有一天,我会重新写下
那些令我慌乱的日子
一笔一画地写
用最好的纸和笔
像在历史中自沉时那样写
像被声音抛弃时那样写
像被时间觊觎时那样写
像毫无希望时那样写
我将写出爱情在草籽里越冬的样子
写她枕着风声入睡
写她猜想雪在头顶积了有多深
写她想到初融雪水的寒凉
身体就颤抖不已
光年
他们说,要有光
于是就有光疾驰而至
从黑色的队伍里找出一些种子
星星的种子、水晶的种子、紫云英的种子
他们开始低语,开始在一片夏夜的回声里
上升,并越过平流层
开始在我们的视力无法抵达的地方值班
他们大部分时候变成了一片模糊的光斑
他们的尾焰每年秋天变成黄叶从天而降
我们知道他们还在
知道那些澄澈之夜流星叫醒我们的时候
有些人已经烧掉了自己
我们活着,就是在等候他们的消息时发芽
在晦暗的山岗上长出灯火和焰火
为回来的人导航
我们的历史,就是用等候刻录的光年
7月21日夜
我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
花园坐在7月21日的深夜里
星群垂落像十万盏吊灯
风中细语如一片激动的水晶
我想到人类的年龄
想到每一天都有人去天上挂一盏灯
该有多少光亮垂怜我们
该有多少挂灯者化作远远的雷声
我想到此刻还有人坐在星群之下
想到岁月该如何走上正义之途
让痛苦不再背叛前世的痛苦
让时间宽待来世的时间
我想到深海有蓝鲸歌唱
深空有土星圆舞
而我身边的草丛里
渴睡的天牛安卧故国
是的,此刻我感到宁静
感到我闭上眼睛
已将万物揽在怀中
信
那封信一直没有写完
雷雨交加的傍晚
我去房顶值班
那里有个巨大的伤口
看得见星星的伤口
如今被爱情出卖
和夜雨撞个满怀
在雨水中我感觉不到哭泣
感觉不到泪水颤抖的羞愧
就那样站在那里
站在长信的半途
站在无人接收的地方
信总是形单影只
夜晚的洋面上
一只纸帆就那么出发了
投奔沉没的道路
而我留在码头上
留在天井敞开的伤口里
留在星群雪崩般的坠落中
复活让我停止死亡
我的指节敲击那些铭文
创面粗糙的铭文
泉水一样渗出血液的铭文
是谁把异世的咒语刻在里边了
喊声暗哑
钝钝地击打我的腹部
一串紧追不舍的回声
如同石头里蜷曲的魂魄
紧紧地抱着一个干缩的吻
直到今夜
记忆复活了一把刀子
粗钝不堪的刀子
在时间的墙面上
重新刻录那个故事
直到今夜
故事复活了一个人
被时间掩埋的人
从历史的渊薮里爬了出来
作者简介:任白,吉林省吉林市人。诗人、画家,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诗集《耳语》《情诗与备忘录》《灵魂的债务》《任白诗选》、中短篇小说集《失语》等。